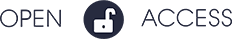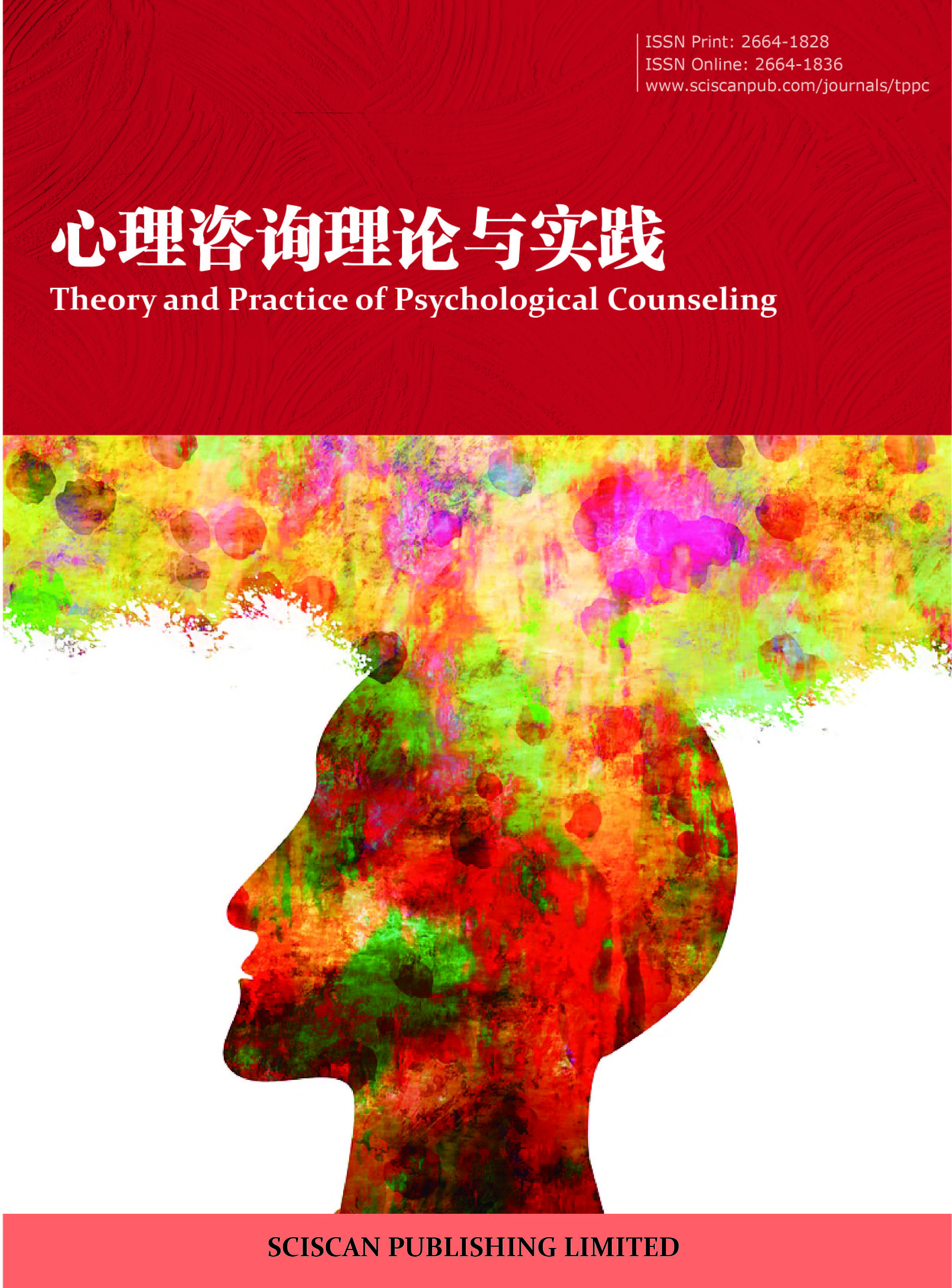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焦虑障碍与抑郁: 焦虑是基础吗?
Anxiety disorders and depression:Is anxiety a basis?
- Authors: 冯萌萌¹ 周广东¹²³*
-
Information:
1.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天津;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天津; 3.国民心理健康评估与促进协同创新中心,天津
-
Keywords:
Anxiety; Anxiety disorder; Depression; Phobia;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焦虑; 焦虑症; 抑郁症; 恐怖症; 强迫症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ving, people's pressure is increasing, accompanied by a variety of emotions, of which anxiety is themost common one. Anxiety disorder is also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all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there are co-morbidities with other anxiety disorders and depression. So, Will anxiety be the basis of these co-morbidity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pathogenesis of anxiety disorder,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hobia and depression, combs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the above-mentioned mental disorders, in order to explore whether anxiety is the common cause of their occurence. It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nxiety and clinical diagnosis.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伴随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其中焦虑是最常见的一种,焦虑症也是目前所有心理健康问题中发病率最高的,且和其他的焦虑障碍及抑郁都存在共病现象。那么,焦虑会是这些共病心理问题的发病基础吗?基于此,文章在简要回顾有关焦虑症、强迫症、恐怖症及抑郁症的临床症状、发病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它们各自的诊断标准重新进行梳理,重点介绍焦虑与上述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以探讨焦虑是否是其发病的共同原因,为更好地认识焦虑和临床诊断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 DOI: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09032
-
Cite:
冯萌萌,周广东.焦虑障碍与抑郁 : 焦虑是基础吗?[J].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2019,1(9):462-480.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09032
1 引言
焦虑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很多因素都可能引起焦虑。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生活中的应激因素也随之增加。因此心理不适应、睡眠障碍等焦虑反应也就随之产生。焦虑目前被定义为一种迫在眉睫而又不知所从的、与危险感有关的、不愉快的情绪[1],主要表现为情绪不佳,还有可能伴随着一定的躯体反应,如口干、出汗、心悸等典型的症状。正常人在预期到将要发生不利的情况时可能会产生焦虑,但是这种焦虑通常不会构成疾病;如果长期的焦虑不能够很好地应付和解除,就会发展成某些精神疾病[2]。
目前,对于一种精神疾病的诊断常常是根据它的核心症状或潜在的病理机制,而有的症状可能表现在多种疾病中,这样很容易导致误诊,或是忽略疾病的核心症状,从而延长患者病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它们的核心症状及其相同之处。如目前的大多数文章和临床都提到了某些精神疾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有些文章也提出焦虑可能是诱发某些疾病的原因;通过整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简称DSM-5,2013),发现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诊断就有一些相似之处,如焦虑情绪、睡眠障碍、注意力难以集中等;但二者又有不同的核心症状。另外,当下发病率较高的恐怖症和强迫症也与焦虑有一定的关系,需要加以区分。因此,本文会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恐怖症的诊断标准、发病原因出发,重点介绍焦虑与它们的关系,进而探讨四者共同的致病机制。
2 焦虑症
2.1 核心症状
焦虑症的临床症状表现为身体和心理症状。其中身体症状主要为头痛、肌肉紧张、心跳过速、震颤等;而心理症状主要表现为烦躁不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易怒、无助感和睡眠障碍等[3]。在DSM-5中,焦虑症的核心诊断标准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时间上至少持续6个月;情绪上对一些事件或活动(如工作或学校表现)呈现过度的焦虑和担心(预期焦虑);认知上患者发现很难控制自己的担忧;生理上对下列症状同时存在3个或以上:思想难以集中、容易疲劳、坐立不安、肌肉紧张、易怒和睡眠障碍等。从上述症状可以看出,焦虑与焦虑症有很大的关系。
2.2 焦虑症与焦虑的关系
从焦虑的角度出发,对于焦虑症的起因、症状,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证据。
行为学派认为条件刺激诱发了个体生理方面的焦虑情绪,进而引发焦虑症。具体为当个体处于焦虑的情境时感到危险,便会激活交感神经,同时诱发海马边缘系统的“中缝核”兴奋,从而产生焦虑反应。另外,个体还受到泛化现象的影响,即患者会受到相似的情境或线索的提示(如只出现了当时情境的一个线索),导致相应区域多次被激活,形成了一种条件性反射,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境,就会产生病理性反射性焦虑症[4]。
遗传研究表明,同卵双生子的患病率为50%,异卵双生子仅为5%;焦虑症患者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常有焦虑人格,家庭发病率为15%[5]。另外,基因方面表明,直系亲属患有焦虑问题的个体易患此障碍,如目前研究较多的BDNFVal66Met基因[6]和COMTVal158Met基因[7]。
还有一部分研究从认知的角度考虑焦虑症的起因,认为焦虑并非由具体的、实际的威胁引起,而是产生了一种没有明确客观和具体的认知作为中介因素,如熊红芳等人[8]认为绝对化要求、概括化评论和挫折耐受的非理性信念(如对自己身体反应进行夸大化且糟糕的解释)引起了焦虑。焦虑症患者会采用一些应对策略,包括成熟或积极的应对策略(求助、寻求社会支持等)或是不成熟的策略(自责、回避、幻想、合理化等),若是选择成熟的策略则会保护和减少患者的症状,采用不成熟的策略将会加重焦虑情绪[9]。
此外,依恋理论认为安全性依恋可能会避免抑郁或焦虑障碍,而不安全依恋则是致病的一种危险因素[10]。Marganska, Gallagher和Miranda[11]对284例焦虑症患者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安全性依恋患者的焦虑和情绪失调症状较轻。另有研究表明,易怒性能够强有力地预测焦虑的严重程度,可作为焦虑诊断的一个临床指标[12]。但是目前,工作记忆训练是否能减少焦虑症状结论还不明确,应用也不多而且研究很少针对焦虑障碍[13]。
3 抑郁症
3.1 核心症状
抑郁症是一类以低落心境为核心的情绪障碍。其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悲伤、易怒,同时伴随着多种认知和躯体症状,如体重变化、睡眠障碍、精神失调等,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功能,患者总是反复关注自身的抑郁症状以及造成抑郁的原因和结果,特别是聚焦于其中的消极感受和负面信念,从而使自己更加焦虑。根据DSM-5,抑郁症明显不同于焦虑症的核心症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时间上至少维持两周的几乎每天的抑郁情绪,兴趣或快乐丧失;生理上食欲不振或贪食,明显的体重增加或减少;从未有过躁狂发作,几乎每天有精神运动性迟钝;认知上低自尊、感觉毫无价值或过度的内疚(严重时会有反复的死亡想法)等。
3.2 抑郁症与焦虑的关系
从上述的症状我们可以看出,抑郁症的焦虑症状虽不太明显,但是抑郁的症状却可以诱发焦虑症状。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在多数情况下,发病后脱离所处的情境后,病情能够得到缓解,但是愈后反复发作的几率较高,多次发作将导致患者的睡眠、生活质量急剧下降且容易发怒,进而引发焦虑症状[14]。
另外,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抑郁与焦虑的关系,比如,研究发现,高神经质的抑郁症患者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更易表现出焦虑症状[15]。负性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等都可能会导致焦虑水平升高,进而加重抑郁症状[16]。
当前,国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抑郁症人群。具体表现为,抑郁症患者大都会有焦虑症状[17],大约占抑郁症人群的60%~90%,其中符合诊断标准的焦虑障碍约为50%[18]。例如,何小婷等人[16]对729例抑郁症患者进行评估,发现其中焦虑症状(诊断标准:HAMA>14分)的发生率为58.85%,且躯体性焦虑比精神焦虑严重。大量研究表明,焦虑和抑郁相伴而生的频率很高,且当个体遭遇其他危险因素时,对焦虑和抑郁都有促发作用。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抑郁水平较高的个体,对早期抑郁和焦虑患者的研究较少。另外,该领域在神经影像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补充。
4 焦虑与抑郁共病
4.1 核心症状
在临床上,抑郁症与焦虑障碍的共病症状主要表现为体重减轻、睡眠障碍、精力减退和绝望感的认知障碍。但在抑郁心境、失去兴趣、认为自己无价值等方面与非共病患者(抑郁症患者)无差异[19]。在DSM-5中,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相同之处如下:身体上很容易疲劳或是精力减少;睡眠障碍(失眠、嗜睡,或是睡眠质量低);认知上注意力难以集中、犹豫不决或是大脑一片空白;在社会、职业或是其他重要功能领域中引起了临床上显著的痛苦或损伤。
在共病状态下,患者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核心症状肯定会有所表现,同时以上描述的症状会加重,因此,可以将单纯患抑郁症或焦虑症患者的上述症状与共病患者的症状进行比较,这将会有利于共病障碍的临床诊断。
4.2 可能的发病机制
焦虑症患者处于一种强烈的焦虑唤醒状态,而抑郁症则是一种情绪低落、低唤醒的状态,二者本来没有任何关系,但焦虑和抑郁却倾向于同时出现,并且它们有很高的正相关(r=0.62)[20]。相关分析表明焦虑和抑郁是彼此双向的风险因素[21],且这种共病的症状会导致结果恶化和治疗复杂化[22], 如伴有焦虑的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不及单纯的抑郁症患者,且会加重患者的抑郁症状[23]。另外,Cramer等人[24]提出了支持性证据,他们使用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Replication的数据分析了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症状,结果显示共患诊断症状(注意力难以集中、疲劳、睡眠障碍和DSM-5的诊断标准一致)对合并症有着重要的意义,且有共病障碍的患者症状网络关系更为紧密,即风险较高,容易迅速扩散到其他症状。
目前,对于焦虑症和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传因素、生理因素、心理社会因素等方面。也有其他方面的研究,从临床症状的角度来看,睡眠和疲劳建起了两者共病的桥梁[25]。从认知的角度分析,Spinhoven, Van Hemert和Penninx[26]研究了重复消极思维在多大的程度上介导了焦虑和抑郁的纵向关联,结果表明抑郁症症状的严重性对5年后的焦虑症症状的严重程度具有预测价值(反之亦成立),并且由重复消极思维产生的心理问题在其中起着显著的介导作用。
4.2.1 免疫系统
从焦虑的角度来看,目前对于二者各自的发病机制,涉及且研究较多的是免疫系统、神经递质学等方面。就焦虑症而言,叶刚和汤臻[27]指出首发焦虑障碍的患者外周多个炎性细胞因子升高且和总体的焦虑程度成正相关。实验研究发现,焦虑患者T细胞的活化减少,而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白细胞介素(IL-17)的水平则会增高[28]。此外,Alessandra等人[29]指出蛋白质的氧化修饰(如蛋白水解功能障碍和受损氧化蛋白的积累)可能是影响情绪障碍(如焦虑症和抑郁症)发病的潜在因素。
就抑郁症来说,细胞因子假设不同环境的应激源和有机炎症可能通过炎症过程引发抑郁症。抑郁患者的白细胞介素(IL-1β、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水平明显会提高[30],白细胞功能紊乱或白细胞数量表达升高被认为是抑郁症的潜在标志物[31]。另外,大量文章总结了炎症和神经元可塑性与抑郁症的关系[32]。
综合以上的研究,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的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的升高可能是二者共病的潜在因素。但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
4.2.2 神经递质学
从神经递质学的角度考虑,焦虑症患者的神经系统如GABA系统、去甲肾上腺系统和5-羟色胺系统和正常人存在差异。在中枢系统内相关区域GABA系统被激活时会抑制神经元的兴奋性,表现出抗焦虑活性[33]。动物实验发现电刺激蓝斑区域会增加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可产生明显的恐惧和焦虑症状[34]。另外内分泌功能的紊乱也会引起焦虑,主要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甲状腺(HPT)轴/性腺(HPG)轴。焦虑症患者血浆中的促肾上腺皮质素(ACTH)水平较健康人高[35]。
对于抑郁症来说,前额皮质的去甲肾上腺素神经元的低放电率与抑郁症的疲劳和认知障碍有关。5-羟色胺中的6个亚型5-HT1R、5-HT1AR、5-HT1BR、5-HT2BR、5-HT2CR和5-HT3R可导致焦虑障碍的产生。甲状腺功能减退后能够引起焦虑;性激素含量降低导致HPG轴失调出现焦虑和抑郁的症状[36];此外,大量的研究发现大脑谷氨酸系统与抑郁症的发病有很大关系,谷氨酸靶向药物投入抗抑郁症的治疗目前也正在进行当中[32]。
可见,去甲肾上腺素、HPA和HPG水平都在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有所涉及,有可能是两者共病的原因。但是关于上述所说的原因国内外都很少涉及。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生物学共病原因是最基础的,且和患者情绪、药物治疗有着直接的关系,若能将二者相同的生物学机制明确,并结合分子遗传学,将会有利于临床的治疗。
5 恐怖症
5.1 核心症状
恐怖症强调的是仅发生于接触某种特定情景或事物时出现的一类特殊的害怕。这类害怕不能自主控制且与情境不相称[1]。在DSM-5中,恐怖症的诊断标准为:患者在公共空间、开放或密闭空间等总是有明显的恐惧,因为他们觉得无法处理或得不到帮助,会选择积极避免这些场景。恐怖症注重的是在不同的地点有明显的焦虑和恐惧,病程持续约为6个月,且在情境中恐惧、焦虑或逃避持续存在。
5.2 恐怖症与焦虑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恐怖症主要以恐惧为主,但也与焦虑情绪相伴。如钟明洁等人[37]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对恐怖症患者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患者的躯体焦虑和精神焦虑都明显高于正常人。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回避行为可以解释焦虑和恐惧情绪的维持,高回避行为会增加患者的焦虑情绪,而低限度的回避行为可以缓解或降低焦虑[38]。
目前,对于恐怖症与焦虑的因果关系处于矛盾的状态。一些研究认为先产生恐怖,之后引起焦虑情绪,如患有恐怖症的人进入特定场合才会产生高度的生理唤醒,进而引发焦虑症状,包括脸红、心跳加速等[39]。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恐怖症并不都是因为害怕而产生,而是由于对某个环境产生焦虑情绪,之后导致对情境的恐惧和回避[40]。如学生接触一个全新的环境,在开始阶段往往表现紧张,产生焦虑情绪(如与家长分离的焦虑),如果这种焦虑情绪不能够消退就会引起轻度的学校恐怖甚至逃学的行为[1]。
6 强迫症
6.1 核心症状
在DSM-4中,强迫症从属于焦虑障碍,但是在DSM-5中强迫以及相关障碍被单独列为一个谱系[41],将其列出来是为了与焦虑症进行区分[42]。
强迫症是一种常见的反复出现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的慢性精神障碍。在DSM-5中强迫性意念和强迫性行为被定义为:(1)反复而持续的想法、欲望或意象和重复性行为(如洗手、排序和检查)或心智活动(如祈祷、计数、重复默念字句),某些时候可以认为是闯入的和不需要的,并且对大多数个体造成了明显的焦虑或痛苦;(2)患者企图忽视或压抑这些强迫性意念,或企图以明显过分的某些想法和活动来将其抵消(如进行强迫性行为)。旨在避免或减少焦虑或痛苦,或避免一些可怕的事件或情况,该定义也就是诊断为强迫症的核心症状[42]。
6.2 强迫症与焦虑的关系
强迫症与焦虑也存在一定的关系。约有30%~40%的强迫症患者同时存在焦虑症状,焦虑可能诱发了强迫症,但是目前人们还不能确定强迫症病人的焦虑是由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产生的,还是先有焦虑后有强迫行为和思维[43]。Rebecca,Daniel和Michael[44]认为先有强迫思维,具体为:一种矛盾的自我概念和强迫性信念导致患者产生了焦虑,进而易患强迫症。但是Szechtman和Woody[45]提出的关于强迫症的安全自动模型认为二者同时产生,具体为:安全动机系统会同时激发焦虑正反馈(对潜在危险进行评价)和防卫子系统(检查、清洗等),即焦虑和强迫行为在事件判断后同时产生。
有研究发现,强迫症和焦虑可以相互预测。Hofmeijer-Sevink等人[46]对2125名被试进行4年纵向追踪研究,结果发现强迫症可以预测焦虑症的首发时间、缓解性焦虑症的复发率及当前焦虑的持续时间。反过来,焦虑敏感度可以作为强迫症治疗效果的预测因子,且基线焦虑敏感度与强迫症严重程度有着高相关[47]。
此外,一些因素可以降低或加重由强迫引起的焦虑。从强迫本身来看,强迫思维(个体对闯入性思维产生不适当的评价)使患者体验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或痛苦,但是强迫行为(如洗涤、检查、回忆、默念等)通过不断重复可以降低患者内心的一些焦虑,但行为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闯入性思维带来的焦虑[48]。从外部环境看,较高的家庭适应水平与强迫症焦虑的加重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他们强迫别人参加某种聚会或是强迫别人进行某种回避行为以降低焦虑[49]。另外,从认知角度分析,部分强迫症患者存在焦虑敏感度的认知问题,并起到中介作用,影响睡眠质量,进而加重焦虑[50]。较高水平的成人依恋焦虑可以影响患者的认知,且与强迫症的严重程度呈显著相关,且自我矛盾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44]。
7 讨论
7.1 焦虑与焦虑障碍及抑郁
正常的焦虑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个体产生焦虑,就可以回避危险情境,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但是过度焦虑就会导致焦虑障碍,严重时会诱发两种及以上的并发症。就现有研究来看,焦虑症一般由焦虑引起,并受到遗传和基因(包括高危因素易怒性)、非理性认知(错误信念)及依恋等方面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重焦虑症状。其中,遗传和焦虑人格特质作为高危因素占很大比例,相比于其他焦虑障碍,焦虑症状也是最突出的。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高神经质个体、负性事件及消极的应对方式等可以诱发抑郁症,但焦虑不是诱发抑郁症的一个因素,却可以加重抑郁的症状,且患者的焦虑症状可以预测抑郁的严重程度。伴有焦虑症的抑郁症是比较严重的,治疗期也比较长,且不同研究中由于不同人群分布情况、样本来源的不同及统计方法的差异导致了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共病率有所不同,但这个范围在40%~60%之间,相比其他心理疾病,这二者之间具有最高的共病率[51]。从临床的角度看,睡眠和疲劳可能是二者同时存在的原因,从认知的角度看,消极思维和认知模式在二者起中介作用,但目前关于二者同时存在的原因还处于矛盾中。
恐怖症常与焦虑相伴,如社交恐怖症,但关于恐怖症与焦虑的关系目前也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首先存在焦虑,之后产生恐惧感,进而发展成更严重的焦虑症状;还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先存在恐惧,之后导致生理唤醒,继而产生焦虑。强迫症是较为常见的,但是目前不确定是焦虑引起了强迫心理还是相反的结果,而Woody认为二者同时发生。强迫症一般会伴有焦虑症状的产生,同时有可能会受到自身认知、家庭水平、依恋类型等方面的影响。
总体来讲,焦虑与精神疾病有很大的关系,可能是因,也可能是果。具体来说:焦虑很有可能是焦虑症、恐怖症和强迫症的发病原因之一,而焦虑症、抑郁症、恐怖症和强迫症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反过来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可预测上述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
7.2 焦虑是焦虑障碍及抑郁的基础的其他可能原因
7.2.1 焦虑的基因和遗传性
研究数据显示,与焦虑有关的基因有很多,如5-HT、BDNF、COMT等,而有的基因同时也在其他精神障碍上有所表现,比如强迫、抑郁等。另外,携带有焦虑易感基因的人更容易患有与焦虑相关的精神障碍;其次,相比于异卵双生子来说,同卵双生子的患病率更高;不同家庭中,若父母患有焦虑症,则其孩子患病的概率会增大。
7.2.2 焦虑的易接近性
首先,相对于其他的情绪,焦虑是生活和工作中最容易接触到的情绪。根据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提出的客观性焦虑理论,认为焦虑是精神疾病的核心概念,是对危险的反应,即人们很容易面临客观威胁和环境,进而产生焦虑。如随着信息时代的进步,人们所面对的应激环境和竞争压力越来越多,较于其他情绪,焦虑更易产生。
其次,人们对所处环境的认知存在偏差。根据心理学家埃利斯提出的ABC理论,个体对激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可以产生信念B,从而引发了情绪和后果C,也就是说,部分个体尤其是患者对所遇的事件持有不正确、绝对性、强制性的看法和信念,导致其极易产生焦虑情绪和行为障碍。
7.2.3 焦虑的基础性
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焦虑是一种基本的情绪,个体时时刻刻都会受到存在感丧失的威胁,而对这种威胁的觉知就是焦虑。当个体处于危险或应激情景时,会激活其生理方面的交感神经系统,表现为心跳加速、呼吸加快、瞳孔放大等,而首先被激活的情绪是焦虑和恐惧。另外,有研究发现,躯体焦虑和认知焦虑虽有不同时间变化的特征,但是随着环境的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会愈来愈紧密。
7.2.4 焦虑的共病性
首先,目前的数据表明,焦虑是人类心理失调的最主要和最经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同时焦虑与其他精神障碍同时发生的概率也为最大,这意味着焦虑增加了其他疾病发生的可能。其次,若精神障碍和焦虑共病,会导致患者的症状加重,并延长患者的治疗期。如患者同时患有抑郁症和焦虑障碍,其症状会有明显的加重,治疗过程也会变得复杂,这也为焦虑是基础提供了一个理由。
综上所述,本文的创新性在于,基于对以上研究现状的分析,归纳综合了焦虑障碍及抑郁在症状、诊断标准的相同点,提出了焦虑可能是焦虑障碍及抑郁发病的基础的观点。另外,从焦虑的角度阐述了焦虑障碍和抑郁的共病性及发病机制,再次说明了焦虑可能是二者的基础;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焦虑可能是焦虑障碍及抑郁的基础的其他可能原因。这一观点如果能得到更多实证的支持,可以为更好地认识焦虑与其他相关精神疾病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能为临床诊断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同伴排斥与儿童的攻击行为(TJJX15-020)。
参考文献
[1] Marks I,刘志中.恐怖症及其治疗[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1983,1:9-15.
[2] 徐韬元.焦虑性神经症[J].国外医学参考资料精神病学分册,1975,104-108.
[3] Stein M B,Sareen J.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J].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15,373:2059-2068.https://doi.org/10.1056/NEJMcp1502514
[4] 张清.浅析焦虑症的产生与治疗方法[J].社会心理科学,2013,28(5):3-5.
[5] 陈祉妍,李新影,杨小冬,等.青少年焦虑、抑郁与偏差行为的行为遗传学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4):540-545.
[6] Chen L,Pan H,Tuan T A,et al.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val66met polymorphism influences the association of the methylome with maternal anxiety and neonatal brain volumes[J].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2015,27(1):137-150.https://doi.org/10.1017/S054579414001357
[7] Chang H,Fang W,Wan F,et al.Age-specific associations among functional COMT Val158Met polymorphism,resting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control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J].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19,106:57-64.https://doi.org/10.1016/j.psyneuen.2019.03.020
[8] 熊红芳,李占江.惊恐障碍患者非理性信念、应对方式及其症状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3):382-384.
[9] Heldt E,Blaya C,Isolan L,et al.Quality of life and treatment outcome in panic disorder:Cognitive behavior group therapy effects in patients refractory to medication treatment[J].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2006,75:183-186.https://doi.org/10.1159/000091776
[10] Mikulincer M,Shaver P R.Attachment in adulthood:Structure,dynamics and change[M].2nd ed.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2016.
[11] Marganska A,Gallagher M,Miranda R.Adult attachment,emotion dysregulation,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J].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2013,83(1):131-141.https://doi.org/10.1111/ajop.12001
[12] Cornacchio M D,Crum M K I,Coxe D S,et al.Irritability and anxiety severity among youth with anxiety[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2016,55(1):54.https://doi.org/10.1016/j.jaac.2015.10.007
[13] 潘东旎,李雪冰.工作记忆训练在精神疾病中的应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9):1527-1543.
[14] 杨明华,郭青山,何欣芙,等.文拉法辛缓释片与丁螺环酮在伴焦虑症状抑郁症患者心理康复中的应用观察[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26(12):1770-1773.
[15] 杨艳慧,李素萍.抑郁症患者负性事件与焦虑症状的关系:神经质的调节作用[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2017,11(3):371-374.
[16] 何小婷,孙宁,杜巧荣,等.抑郁症伴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6,42(2):206-210.
[17] 陈子晨,张慧娟,汪新建,等.抑郁症起源的三类理论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8,26(6):1041-1053.
[18] Zhang S J,Qiang Z,Yang X J.Risk factors and levels of comorbidity of mood,anxiety and alcohol-use disorders in residents of Liaoning province[J].Chinese Journey Public Health,2012,28(1):30-32.
[19] 廖震华,王文强,丁丽君,等.抑郁症共病焦虑障碍临床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4,30(5):552-555.
[20] Bandelow B,Michaelis S.Epidemiology of anxiety disorders in the 21st century[J].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2015,17(3):327-335.
[21] Jacobson N C,Newman M G.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 bidirectional risk factors for one another: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7,143(11):1155-1200.https://doi.org/10.1037/bul0000111
[22] Wiethoff K,Bauer M,Baghai T C,et al.Prevalence and treatment outcome in anxious versus nonanxious depression:Results from the German Algorithm Project[J].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2010,71(8):1047-1054.https://doi.org/10.4088/JCP.09m05650blu
[23] 王玉忠.焦虑症状对抑郁症治疗效果的影响[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6,8(6):134-135.
[24] Cramer A O,Waldorp L J,Borsboom D,et al.Comorbidity:A network perspective[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010,33(2-3):137-150.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09991567
[25] Borsboom D,Cramer A O.Network analysis: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the structure of psychopathology[J].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13,9(2):91-121.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050212-185608
[26] Spinhoven P,Van Hemert A M,Penninx B W.Repetitive negative thinking as a mediator in prospective cross-disorder associations betwee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isorders and their symptoms[J].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2018,63:6-11.https://doi.org/10.1016/j.jbtep.2018.11.007
[27] 叶刚,汤臻,李歆,等.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外周炎性细胞因子与焦虑症状的相关性[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6,25(8):709-712.
[28] Grosse L,CarvalhoL A,Birkenhager T,et al.Circulating cytotoxic T cells and natural killer cells as potential predictors for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in melancholic depression.Restoration of T regulatory cell populations after antidepressant therapy[J].Psychopharmacology,2016,233(9):1679-1688.https://doi.org/10.1007/s00213-015-3943-9
[29] Alessandra F,Ferreira F,Bota R G,et al.The role of oxidative stress in anxiety disorder:Cause or consequence?[J].Free Radical Research,2018,52(7):737-750.https://doi.org/10.1080/10715762.2018.1475733
[30] Valkanova V,Ebmeier K P,Allan C L.CRP,IL-6 and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13,150(3):736-744.https://doi.org/10.1016/j.jad.2013.06.004
[31] Hodes G E,Pfau M L,Leboeuf M,et al.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peripheral immune system promote resilience versus susceptibility to social stres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4,111(45):16136-16141.https://doi.org/10.1073/pnas.1415191111
[32] Gulyaeva N V.Interplay between brain BDNF and glutamatergic systems:A brief state of the evid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on[J].Biochemistry (Moscow),2017,82(3):301-307.https://doi.org/10.1134/S0006297917030087
[33] Murrough J W,Yaqub S,Sayed S,et al.Emerging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anxiety[J].Expert Opinion on Emerging Drugs,2015,20(3):393-406.https://doi.org/10.1517/14728214.2015.1049996
[34] Lapierre Y D.Handbook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A biological approach[J].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1996,41(3):289-290.https://doi.org/10.1016/0022-3999(96)00055-4
[35] Musselman D L,Nemeroff C B.Depression and endocrine disorders:focus on the thyroid and adrenal system[J].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Supplement,1996,168(30):123-128.https://doi.org/10.1192/S0007125000298504
[36] 陈兆斌,张博,刘秀敏,等.焦虑症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J].天津中医药,2018,35(4):316-320.
[37] 钟明洁,吕圆圆.上学恐怖症临床特征及诊初探[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5):658-660.
[38] Rudaz M,Ledermann T,Margraf J,et al.The moderating role of avoidance behavior on anxiety over time:Is there a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nd specific phobia?[J].Plos One,2017,12(7):1-14.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80298
[39] Gerlach A L,Mourlane D,Rist F.Public and private heart rate feedback in social phobia:A manipulation of anxiety visibility[J].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2004,33:36-45.https://doi.org/10.1080/16506070310014682
[40] 林雄标,胡纪泽.社交恐怖症患者的认识特征及相关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6):423-425.
[41] 李功迎,宋思佳,曹龙飞.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解读[J].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2014,2(4):310-312.
[42] 朴轶峰.DSM-5强迫及相关障碍解析[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7,4(46):202-203.
[43] 孙凌,王建平.强迫症诊断研究的新变化[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6):1041-1047.
[44] Rebecca S,Daniel F,Michael K.Attachment anxiety and self-ambivalence as vulnerabilities toward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J].Journal of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2018,18:40-46.https://doi.org/10.1016/j.jocrd.2018.06.002
[45] Szechtman H,Woody E.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s a disturbance of security motivation:Constraints on comorbidity[J].Neurotoxicity Research,2006,10:103-112.https://doi.org/10.1007/BF03033239
[46] Hofmeijer-Sevink M K,Batelaan N M,Van Megen H J,et al.Presence and predictive value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in anxiety and depressive disorders[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2017,63(2):85-93.https://doi.org/10.1177/0706743717711170
[47] Blakey S M,AbramowitzJ S,Reuman L,et al.Anxiety sensitivity as a predictor of outcome in the treatment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2017,57:113-117.https://doi.org/10.1016/j.jbtep.2017.05.003
[48] 张众良,张仲明.强迫症病理的认知--行为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2):306-313.
[49] Lebowitz E R,Panza K E,Bloch M H.Family accommodation on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anxiety disorder:A five-year update[J].Expert Review of Neurotherapeutics,2016,16(1):45-53.https://doi.org/10.1586/14737175.2016.1126181
[50] Raines A M,Short N A,Sutton C A,et al.Obsessive compulsive symptom dimensions and suicide:The moderating role of anxiety sensitivity cognitive concerns[J].Psychiatry Research,2015,228(3):368-372.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5.05.081
[51] 吴秀勇,吴效明,彭红军,等.抑郁症及焦虑障碍的磁共振影像学研究进展[J].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2015,28(3):229-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