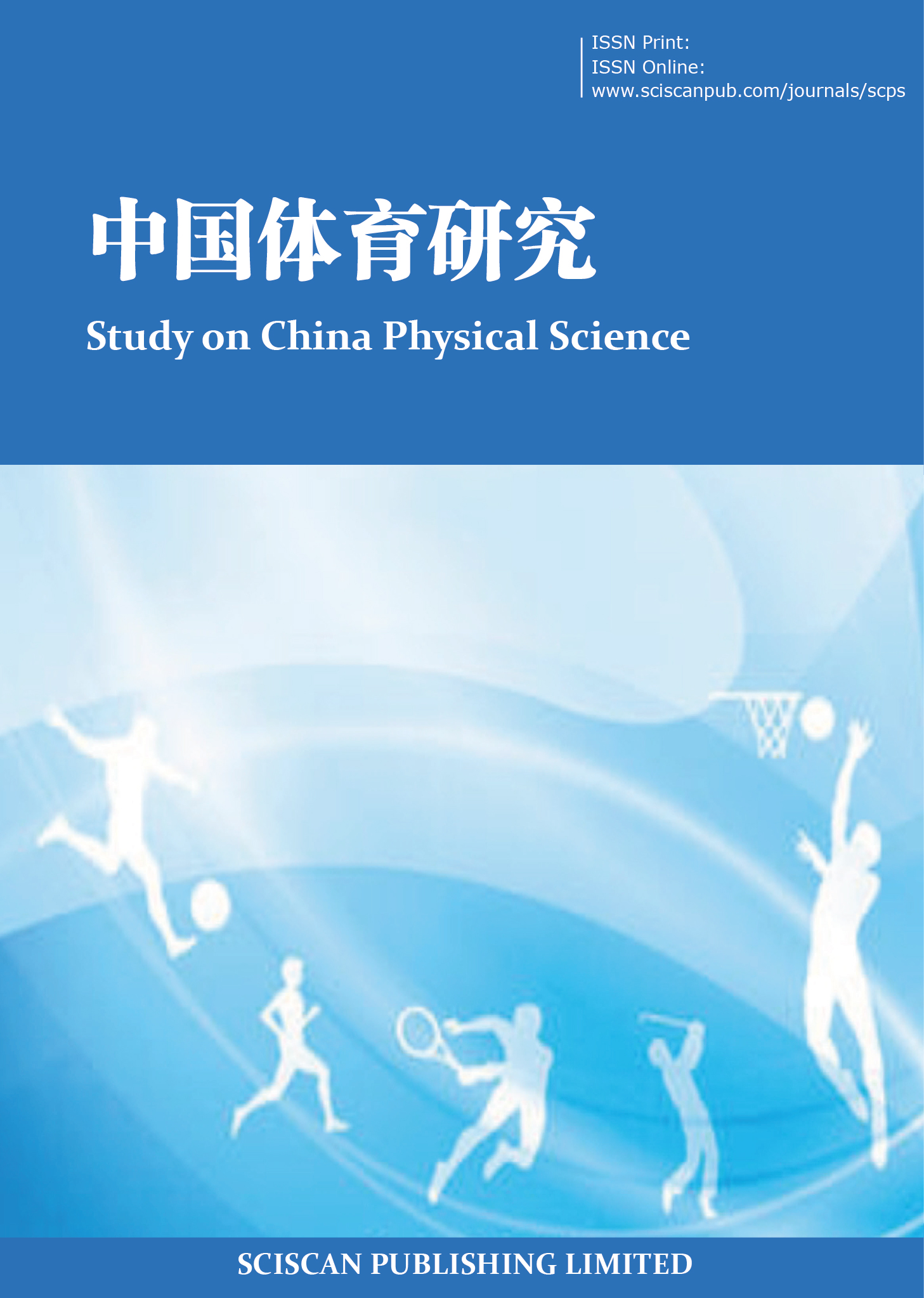Study on China Physical Science
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Support Factors for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among Residents of the Yi Ethnic Area in Heizhugou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 Authors: 王金鹏¹ 郭钊逢¹ 李丹¹ 周全福² 王冰³ 刘勇³
-
Information:
1.成都大学体育学院,成都; 2.四姑娘山管理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四川旅游学院,成都
-
Keywords:
Heizhugou; Ethnic Yi residents; Support for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Influencing factors黑竹沟; 彝族地区居民; 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 影响因素
- 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 This study takes the Black Bamboo Gully area as a case study to conduct a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perception of residents’ support for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in the Yi ethnic area of Black Bamboo Gull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s 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support across variou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ix key factors affecting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support were identified. The study employs parametric testing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to analyze the residents of the Yi ethnic area in Black Bamboo Gully across different genders, ages, income levels, and education levels. Research Conclus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support between genders; residents of different age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st perception and ecological perception;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nse of place, ecological perception, and benefit percep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support among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in ethnic areas and offer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研究目的:本研究以黑竹沟地区为案例,对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感知进行差异分析,以揭示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下的影响因素差异。研究方法: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影响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六个关键因素。研究采用参数检验和方差分析,对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的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性别在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居民在成本感知和生态感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受教育水平在地方感、生态感知和收益感知等方面呈现显著性差异;不同收入在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该研究结果为山地户外旅游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 DOI: https://doi.org/10.35534/scps.0603023
- Cite: 王金鹏,郭钊逢,李丹,等.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中国体育研究,2024,6(3):258-277.
1 引言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1]。目前,民族地区的总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3.80%,比例超过一半。尽管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但旅游业的发展常常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2]。此外,大部分山地地区地形复杂、植被丰富,形成了高山峡谷、高原湖泊、森林草原等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得山地户外旅游成为游客观光和体验的重要方式,而山地户外旅游包括登山、野营、滑雪、攀岩、旅游休闲、观光度假、科考实践、山地探险、山地自行车等活动,是山地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3]。四川省西南部小凉山北坡的黑竹沟地区,是彝族人民的聚居地[4]。该地区因其具有70%的森林覆盖率而被誉为“中国森林氧吧”,又因其神秘性而被称为“中国的百慕大”,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是一个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山岳风景名胜区[5]。而居民作为山地户外旅游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山地户外旅游的支持度与旅游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连,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6]。因此,彝族地区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的支持度对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以黑竹沟地区为例,旨在深入分析黑竹沟地区彝族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存在的差异性。研究结果将为黑竹沟地区乃至其他民族地区的山地户外旅游业提供策略建议,对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实现旅游与社区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主要涵盖两个核心要素:成本与回报。在进行社会交换时,个体必须审慎权衡其所投入的成本与所期待的回报。从本质上讲,如果交换的成本超出了其带来的价值,那么交换就无法顺利进行,这标志着交换的失败;反之,则意味着交换的成功。为了实现有效的社会交换,必须对成本进行合理控制,并确保所获得的价值大于所投入的成本[7]。社会交换理论是阐释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和支持度的一个有效框架。居民通过评估与其他参与者互动的结果来判断旅游发展的价值。因此,居民可能会将户外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视为影响他们之间信任程度的关键因素[8]。在旅游领域,社会交换的成效往往直接反映在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支持程度上。这种态度和支持程度是居民对于旅游业带来的利益与成本进行权衡后的结果,它们揭示了居民如何看待旅游发展对其个人及社区的影响[9]。综上所述,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揭示了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态度的形成机制。居民会根据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本与回报来决定其支持度。有效的旅游发展策略应确保居民从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超过他们所承担的成本,从而增强居民的信任和支持。
2.2 旅游支持度
感知是指个体对特定对象的认知评价、情感反应及行为倾向的总和;而支持度则反映了个体对某一现象或提议在程度上的赞同或拥护[10]。国内学者已从多角度探讨了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如许振晓学者[11]在九寨沟的研究中,将地方感和成本感知纳入理论模型,以解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程励学
者[12]分析了生态感知对农户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强调了增强生态环境感知的重要性;雷硕学者[13]在对国家生态公园生态旅游的研究中发现,收益感知、满意度和参与行为与支持度呈正相关;王咏学者[14]则指出,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度和旅游利益感知对黄山风景区周边社区居民的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本研究综合前人研究,探讨了地方感、收益感知、旅游参与行为、机构信任、生态感知和成本感知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将上述六个变量作为影响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因素。综上,旅游支持度是衡量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重要指标,它涵盖了居民对旅游活动的认知评价、情感反应及行为倾向,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居民的地方感、收益感知、旅游参与行为、机构信任、生态感知以及成本感知等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因此,深入研究和理解这些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对于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2.3 山地户外旅游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公众对于精神层面的满足感需求日益超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这种趋势促使远足、徒步和登山等山地户外运动逐渐成为主流的休闲活动。相应地,这些活动也推动了一种以体验为中心的新型旅游模式——山地户外旅游[15]。尽管山地户外旅游尚未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统一定义,但公众和学术界常将其与户外运动、山地旅游、体育旅游等概念相联系。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界定,山地旅游特指在丘陵和山脉等特定地理环境中,依托其独特的景观、地形、气候以及生物多样性(包括动植物)和当地社区文化,开展的一种特色鲜明的旅游活动。在国际旅游领域,户外旅游通常被细分为户外娱乐、户外休闲、自然旅游和户外探险等多种形式[16]。学者Burch作为山地户外旅游概念的先驱,将其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旅行方式,区别于传统的休闲观光旅游。他强调了山地户外旅游的三个显著特征:首先,这类旅游活动通常在自然环境中展开,使参与者能够直接体验并与自然元素互动;其次,它涉及体育活动的参与,这些活动不仅包括身体锻炼,也涵盖了一系列技能和体能挑战;最后,它以休闲和娱乐为导向,旨在为旅游者提供一种从日常生活和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休闲体验[17]。山地户外旅游相关的户外活动的典型例子是攀岩和攀冰、登山、山地滑雪、激流皮划艇和漂流、峡谷、山地自行车、冲浪、跳伞、滑翔伞和定点跳伞等户外运动,而目前国内对山地户外旅游的研究较少,大多集中在山地户外旅游目的地以及游客满意度[18]等方面。综上所述,目前大多数学者还集中在山地户外旅游满意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主客关系视角下在游客方面的研究,但是作为当地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差异研究较为欠缺。
3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提取公因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确定变量之间潜在的因子结构。在因子分析中,首先需要考虑Cronbach’s alpha值和KMO值来评估测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然后进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以探究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接着进行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以确定相关系数。最后采用方差分析法将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别与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的各维度进行差异分析。
3.1.1 EFA分析
在研究中,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确定变量之间潜在的因子结构[19]。在因子分析中需要考虑Cronbach’s alpha值和KMO值来评估测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
3.1.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研究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衡量两个因素相关密切程度的一种分析方法[20]。旨在分析影响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
3.1.3 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ANOVA)是统计学中用于评估三个或更多样本均值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方法。该技术通过分析数据中的总变异性,并将其归因于不同因素,从而确定特定变量的不同水平是否对观察结果产生显著影响[21]。在本研究中,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三个类别变量及以上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探求其组间差异与组内差异。
3.2 数据来源
问卷调研时间为2023年3月2日至23日。调研对象为黑竹沟地区及周边的居民。支持度等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数值1到5分别对应“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问卷预调研收回82份问卷,针对性地对题项进行调整后再次发放,最终完成问卷34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取315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2.64%。测量题项如表1所示,且测量题项均来自前人的成熟量表。地方感、收益感知借鉴蒋卓芮学者的研究[22],成本感知借鉴程励学者的研究,生态感知维度借鉴姚治国学者的研究,机构信任、参与行为维度借鉴吴蓉学者的研究[23]。
表 1 测量题项的量表来源
Table 1 Scale sources of measurement items
|
变量 |
测量题项 |
量表来源 |
|
地方感 |
A1有强烈的归属感 |
蒋卓芮,2021 |
|
A2感情胜过其他地方 |
||
|
A3是理想的生活地方 |
||
|
A4旅游开发比较舒适 |
||
|
A5黑竹沟地区使个人比较依恋 |
||
|
收益感知 |
B1旅游开发提高了生活水平 |
蒋卓芮,2021 |
|
B2旅游开发提高了经济收入 |
||
|
B3山地户外旅游发展了就业率 |
||
|
B4山地户外旅游改善了公共事业 |
||
|
参与行为 |
C1参与景区管理与治理 |
吴蓉,2021 |
|
C2能开展自主经营活动 |
||
|
C3参与景区旅游政策的讨论 |
||
|
C4旅游开发能更好地就业 |
||
|
机构信任 |
D1旅游开发对本地有益 |
吴蓉,2021 |
|
D2政府开发不会滥用权力 |
||
|
D3旅游公司对当地态度比较友好 |
||
|
生态感知 |
E1山地户外旅游开发增强了环保意识 |
姚治国,2022 |
|
E2发展旅游改善了居住环境 |
||
|
E3发展旅游提升了村容村貌 |
||
|
成本感知 |
F1发展山地户外旅游提高了生活成本 |
程励,2023 |
|
F2旅游开发造成了环境破坏 |
||
|
F3旅游开发增大了贫富差距 |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问卷调查中人口统计学部分的特征如下:男性占比63.81%,女性占比36.19%。对于年龄的调查,基本覆盖了各个年龄阶段。20岁以下的占22.53%,21~30岁的占比29.84%,31~49岁的占比23.49%,50岁以上的占比24.12%。由年龄分布可说明黑竹沟居民的年龄阶段主要分布在21~30岁和50岁以上,这可能是因为21~30岁年龄阶段人群大多在景区参与旅游相关工作,50岁以上人群,皆为常住人口,在此地养老。月收入方面,1000元以下占26.34%,1001~2000元占28.57%,2001~3000元占17.77%,3001~5000元占18.73%,5000元以上占8.57%。大多数人月收入在1000~3000元水平,说明黑竹沟的旅游开发对于居民的收入确实有一定影响。学历方面,小学及以下占7.61%,初中占22.53%,高中占63.80%,专科及以上占6.03%,黑竹沟地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主要分布在高中学历。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通过KMO检验值0.885和显著性水平0.000*确保数据的适宜性[24]。本研究问卷共有22个测量题项,测量问卷的总体Cronbachs α=0.828,大于0.7,KMO值=0.885,大于0.7,且Bartletts球形检
验=6737.217,自由度=378,在P=0.000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研究地方感、收益感知、参与行为、机构信任、生态感知、成本感知等六个测量维度内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过程通过SPSS 26.0对因子进行降维,继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的最大方差法。根据旋转后因子矩阵,基于因子特征大于1,不存在标准化载荷小于0.5的题项。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可以得知,共提取6个公因子,然后对因子分析结果进行合并取均值对变量命名。地方感等六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因子的累计总方差为76.201%,大于60%。(详细见表2)
表 2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
续表 |
||||
|
变量 |
测量题项 |
标准化因子载荷 |
方差解释% |
克隆巴赫 |
|
变量 |
测量题项 |
标准化因子载荷 |
方差解释% |
克隆巴赫 |
|
地方感 |
A1 |
0.799 |
39.312 |
0.869 |
|
A2 |
0.765 |
|||
|
A3 |
0.757 |
|||
|
A4 |
0.711 |
|||
|
A5 |
0.708 |
|||
|
收益感知 |
B1 |
0.887 |
49.618 |
0.919 |
|
B2 |
0.827 |
|||
|
B3 |
0.824 |
|||
|
B4 |
0.801 |
|||
|
参与行为 |
C1 |
0.833 |
57.237 |
0.903 |
|
C2 |
0.826 |
|||
|
C3 |
0.785 |
|||
|
C4 |
0.774 |
|||
|
机构信任 |
D1 |
0.842 |
68.056 |
0.878 |
|
D2 |
0.780 |
|||
|
D3 |
0.735 |
|||
|
生态感知 |
E1 |
0.808 |
72.567 |
0.896 |
|
E2 |
0.798 |
|||
|
E3 |
0.733 |
|||
|
成本感知 |
F1 |
0.764 |
76.201 |
0.863 |
|
F2 |
0.746 |
|||
|
F3 |
0.728 |
|||
|
总体 KMO=0.885 Bartletts球形检验=6737.217 自由度=378 Sig.=0.000 |
||||
|
Cronbachs α= 0.828 总体解释方差=76.201% 项数22 |
||||
4.3 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即是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探索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研究方
法[25]。根据表3所展示的统计结果,可以明确指出各维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旅游支持度与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50、0.448、0.367、0.470、0.516和0.363,其中大部分相关系数大于0.3,这表明各维度与旅游支持度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因此,可以认为各变量与旅游支持度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关系(详细见表3)。
表 3 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
续表 |
||||||||
|
变量 |
M±SD |
A |
B |
C |
D |
E |
F |
G |
|
变量 |
M±SD |
A |
B |
C |
D |
E |
F |
G |
|
收益感知 |
3.20±0.96 |
1 |
||||||
|
成本感知 |
2.52±0.76 |
0.471** |
1 |
|||||
|
机构信任 |
2.50±0.76 |
0.467** |
0.584** |
1 |
||||
|
生态感知 |
2.49±0.84 |
0.351** |
0.526** |
0.477** |
1 |
|||
|
参与行为 |
3.49±0.97 |
0.267** |
0.504** |
0.388** |
0.498** |
1 |
||
|
地方感 |
4.35±0.90 |
0.481** |
0.375** |
0.424** |
0.517** |
0.340** |
1 |
|
|
旅游支持力度 |
2.64±0.64 |
0.250** |
0.448** |
0.367** |
0.470** |
0.516** |
0.363** |
1 |
注:A=收益感知;B=成本感知;C=机构信任;D=生态感知;E=参与行为;F=地方感;G=旅游支持度;** 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4 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
4.4.1 不同性别居民对民族地区山地户外旅游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从表4可知,不同性别黑竹沟地区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在地方感、收益感知、参与行为、机构信任、生态感知、成本感知方面。通过P值结果得知,P>0.05,不同性别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显著性分析结果表示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民族地区不同性别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不存在明显影响。
表 4 不同性别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factors influencing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support by gender
|
影响因素 |
性别 |
F |
P |
方差齐性检验 |
|
|
男性 |
女性 |
||||
|
成本感知 |
201 |
114 |
0.071 |
0.946 |
是 |
|
地方感 |
201 |
114 |
0.018 |
0.814 |
是 |
|
机构信任 |
201 |
114 |
0.038 |
0.756 |
是 |
|
参与行为 |
201 |
114 |
0.020 |
0.816 |
是 |
|
生态感知 |
201 |
114 |
0.049 |
0.417 |
是 |
|
收益感知 |
201 |
114 |
0.185 |
0.607 |
是 |
4.4.2 不同年龄居民对于民族地区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年龄居民感知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不同年龄样本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得知:不同年龄居民对成本感知的平均分呈现水平显著性(F=1.881,P=0.133);不同年龄居民对生态感知的呈现水平显著性(F=3.583,P=0.014)。
表 5 不同年龄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factors influencing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support by age group
|
年龄 |
N |
成本感知 |
地方感 |
机构信任 |
参与行为 |
生态感知 |
收益感知 |
|
1 |
71 |
2.338 |
4.2782 |
2.3944 |
3.3768 |
2.25 |
3.1021 |
|
2 |
94 |
2.5691 |
4.383 |
2.5479 |
3.5532 |
2.6676 |
3.2074 |
|
3 |
74 |
2.6149 |
4.2905 |
2.5642 |
3.5743 |
2.5439 |
3.1318 |
|
4 |
76 |
2.5428 |
4.4539 |
2.4868 |
3.4474 |
2.4441 |
3.3553 |
|
F |
1.881 |
0.633 |
0.758 |
0.683 |
3.583 |
1.014 |
|
|
P |
0.133 |
0.594 |
0.519 |
0.563 |
0.014 |
0.387 |
|
注:1表示20岁以下,2表示21~30岁,3表示31~50岁,4表示50岁以上。
4.4.3 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对成本感知与生态感知因素在不同年龄居民之间两两比较
根据表6的组内差异结果,可以发现20岁以下居民与31~49岁居民在成本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P=0.030,P<0.05),而20岁以下居民与50岁以上居民在成本感知上则无显著性差异。同样,20岁以下居民与21~30岁居民在成本感知方面也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此外,21~30岁居民与31~50岁居民在成本感知上的差异也不显著,31~50岁居民与50岁以上居民在成本感知方面同样没有显著性差异。在生态感知方面,20岁以下居民与21~30岁居民(P=0.002,P<0.05)以及20岁以下居民与31~50岁居民(P=0.034,P<0.05)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然而,21~30岁居民与31~50岁居民、21~30岁居民与50岁以上居民,以及31~50岁居民与50岁以上居民在生态感知方面的差异均不显著。该发现表明,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在成本感知和生态感知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生活经验、教育背景和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
表 6 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对成本感知与生态感知因素在不同年龄居民之间两两比较
Table 6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st perception and ecological perception factors among resident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he black bamboo gully Yi Ethnic area
|
组内差异 |
成本感知(P值) |
生态感知(P值) |
|
a与b |
0.055 |
0.002 |
|
a与c |
0.030 |
0.034 |
|
a与d |
0.105 |
0.105 |
|
b与c |
0.700 |
0.339 |
|
b与d |
0.823 |
0.082 |
|
c与d |
0.700 |
0.463 |
注:表中a表示20岁以下,b表示21~30岁,c表示31~50岁,d表示50岁以上。
4.4.4 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对于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差异进行分析。如表7所示,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对旅游影响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可知: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对地方感的平均分呈现水平显著性(F=2.710,P=0.045);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对生态感知的平均分呈现水平显著性(F=2.305,P=0.028);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对收益感知的平均分呈现水平显著性(F=2.485,P=0.061)。
表 7 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Table 7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factors influencing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support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level
|
收入 |
N |
成本感知 |
地方感 |
机构信任 |
参与行为 |
生态感知 |
收益感知 |
|
1 |
24 |
2.6771 |
4.625 |
2.7813 |
3.6563 |
2.5417 |
3.625 |
|
2 |
71 |
2.6056 |
4.2782 |
2.4965 |
3.493 |
2.5669 |
3.1549 |
|
3 |
201 |
2.4988 |
4.393 |
2.4876 |
3.5075 |
2.5025 |
3.2015 |
|
4 |
19 |
2.25 |
3.8947 |
2.3289 |
3.1316 |
2.0132 |
2.8421 |
|
方差齐性检验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
F |
1.478 |
2.710 |
1.431 |
1.114 |
2.305 |
2.485 |
|
|
P |
0.221 |
0.045 |
0.234 |
0.344 |
0.028 |
0.061 |
|
注:1表示小学以下学历,2表示初中学历,3表示高中学历,4表示专科及以上学历。
4.4.5 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之间在地方感、生态感知、收益感知因素的两两比较
根据表8的方差分析结果,本研究揭示了黑竹沟地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地方感、生态感知、收益感知等因素的影响关系。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在地方感因素上对居民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小学以下与专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居民在地方感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8),以及高中学历与专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居民在地方感方面同样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0.021)。其他教育水平之间的比较未发现显著性差异。在生态感知方面,受教育程度同样显示出显著性影响(P<0.05),具体表现为小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居民与专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居民在生态感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0)、初中学历与专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居民在生态感知上也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0.011),以及高中学历与专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居民在生态感知方面的显著性差异(P=0.015)。其他教育水平组别间未观察到显著性差异。对于收益感知因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5),其中小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居民与初中(P=0.040)、高中(P=0.043)及专科及以上(P=0.009)教育水平的居民在收益感知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教育水平组别间的比较未发现显著性差异。综上,黑竹沟地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在地方感、生态感知、收益感知等维度上均表现出显著性影响,这提示了教育水平对于居民对旅游发展相关因素感知的重要性。
表 8 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之间在地方感、生态感知、收益感知因素的两两比较
Table 8 Pairwise comparisons of locality sense, ecological perception, and benefit perception factors among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
组内差异 |
地方感(P值) |
生态感知(P值) |
收益感知(P值) |
|
a与b |
0.101 |
0.898 |
0.040 |
|
a与c |
0.230 |
0.828 |
0.043 |
|
a与d |
0.008 |
0.040 |
0.009 |
|
b与c |
0.352 |
0.577 |
0.726 |
|
b与d |
0.097 |
0.011 |
0.209 |
|
c与d |
0.021 |
0.015 |
0.121 |
注:表中a表示小学以下学历,b表示初中学历,c表示高中学历,d表示专科及以上学历。
4.4.6 不同收入居民对于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结果如表9显示: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因素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因此,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因素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表 9 不同收入水平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Table 9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factors influencing 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support by income level
|
收入 |
N |
成本感知 |
地方感 |
机构信任 |
参与行为 |
生态感知 |
收益感知 |
|
1 |
83 |
2.4940 |
4.4006 |
2.5843 |
3.5181 |
2.4849 |
3.2319 |
|
2 |
90 |
2.5306 |
4.3583 |
2.4389 |
3.5444 |
2.5361 |
3.2361 |
|
3 |
56 |
2.4821 |
4.2634 |
2.4598 |
3.3616 |
2.5089 |
3.0446 |
|
4 |
59 |
2.5636 |
4.4068 |
2.5551 |
3.589 |
2.4534 |
3.2627 |
|
5 |
27 |
2.5648 |
4.2778 |
2.4352 |
3.3056 |
2.3981 |
3.1852 |
|
方差齐性检验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
F |
0.132 |
0.294 |
0.559 |
0.723 |
0.182 |
0.473 |
|
|
P |
0.971 |
0.882 |
0.692 |
0.577 |
0.948 |
0.756 |
|
5 研究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5.1.1 黑竹沟彝族地区不同性别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差异
本研究对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的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进行人口统计学分析,发现性别在支持度上无显著差异。社会交换理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解释,指出在该地区彝族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在性别上保持一致。凉山彝族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以及由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程,形成了彝族保守且封闭的民族性格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体系。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概念[26],如互惠性、信任和期望,在彝族居民中形成共鸣,促进了性别间对旅游态度的一致性[27]。在这种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彝族居民在对山地户外旅游的支持度上表现出一致性。
5.1.2 黑竹沟彝族地区不同年龄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差异
在生态感知方面,本研究发现在不同年龄对生态感知影响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李志苗[28]学者对生态移民影响感知研究的结果一致,证明不同年龄居民对生态感知影响因素均存在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老一辈彝族居民通过传承传统文化,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以生活经验教导下一代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相比之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一代接触到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注重个人利益和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关注不足。
在成本感知方面,本研究与韩磊学者[29]对恩施州地区的环境成本、经济成本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在成本感知因素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实地调查发现,从事山地户外旅游服务的居民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受过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愿意从事与山地户外旅游相关的工作。相对而言,年长者更依赖传统农耕生活或传统行业,收入较低,对成本的敏感度较低。与此相反,年轻一代接触到现代化经济和更多就业机会,相对收入较高,对成本感知因素的关注度较高。因此,不同年龄层在成本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5.1.3 黑竹沟彝族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差异
据人口学统计特征得知,黑竹沟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大部分处于3000元以下,这种现象在彝族人民中较为普遍,原因是受到封闭且交通不便的大山环境的影响。其中,居民主要通过“打笋”这一传统方式获取收入,且每天的平均工资仅为100~200元。在研究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在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因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以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解释:互惠性的农业生产活动,在时间和劳动成本上投入较多,是维持社会交换的一种形式。
5.1.4 黑竹沟彝族地区不同受教育水平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差异
在地方感方面,本研究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对地方感知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方德敏[30]等人对九寨沟地区地方感研究相符,这呼应了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观点,即公正原则[31]。在生态感知方面,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参加户外旅游的思维导向、信息分析能力等素养,这也势必影响其对旅游生态标签的看法和感知度[32]。可能因为黑竹沟地区的彝族居民教育水平和生态环境意识之间相对差异比较大,一部分是未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老年人,另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由此导致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感知因素存在差异。在收益感知方面,教育程度较高的彝族居民可能更加注重个人经济收益和发展。这也符合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即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可能塑造个体的态度和价值观产生不同,从而影响其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期望[26]。
5.2 结论
本文从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对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在旅游支持度上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当地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和社会制度的跨越有关,导致男性和女性在旅游感知和态度上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年龄对生态感知的影响显著。其中,老一辈居民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生态环境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较强的保护意识,而年轻一代则可能因更多接触现代化经济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成本感知方面,年轻一代显示出更高的关注度,这可能与他们更多地接触到现代化经济和就业机会有关,而年长者由于依赖传统农耕生活,对成本的敏感度相对较低。此外,收入水平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当地居民普遍依赖有限的农业生产活动有关。而受教育水平则显著影响居民的地方感、生态感知和收益感知,其中高学历居民表现出更强的地方依恋、文化识别能力以及对生态和收益的敏感态度。
5.3 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黑竹沟彝族地区居民对山地户外旅游支持度的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策略性建议:首先,强化性别平等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女性群体在旅游产业中的自我认知与参与度。建议通过政府主导的公共宣传活动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积极形象塑造,深化性别平等观念的社会认同。其次,建议地方政府出台经济激励政策,构建旅游服务领域的奖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从业者予以物质奖励及荣誉认定,以此激发更广泛的居民群体投身于旅游服务行业。最后,建议设立山地户外旅游教育与培训中心,开展职业培训项目,降低教育门槛,确保培训内容的实用性与针对性,旨在促进黑竹沟地区的综合发展及旅游产业人才的培育。
参考文献
[1] 李鹏,邓爱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旅游业的新使命和新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3(8):41-46.
[2] 刘勇,何丽.旅游标准化建设促进我国山地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以西部藏族聚居区四姑娘山景区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22(8):22-30.
[3] 龚剑.山地户外旅游对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以四川省四姑娘山为例[J].四川体育科学,2023,42(4):92-96,133.
[4] 杨海蒂.黑竹沟[J].经营管理者,2023(2):102-104.
[5] 闫丽丽,杨青林,黄中奕,等.山地景区生态旅游适宜性分析及功能区划——以黑竹沟风景名胜区为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3(1):123-131.
[6] 赵雪雁,李东泽,李巍,等.高寒民族地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及影响因素——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生态学报,2019,39(24):9257-9270.
[7] 袁箐,陈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居民地方意象对其节庆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16-128.
[8] 孙凤芝,贾衍菊.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下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4):90-99.
[9] 贾衍菊,李昂,刘瑞,等.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3):171-183.
[10] 银松,李瑞,殷红梅.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村寨居民地方性感知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雷公山地区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23,32(3):144-156.
[11] 许振晓,张捷,Geoffrey Wall,等.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J].地理学报,2009,64(6):736-744.
[12] 程励,魏秀蓉,普片.生态走廊带农户旅游获益与成本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分析[J].农村经济,2023(4):137-144.
[13] 雷硕,甘慧敏,郑杰,等.农户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认知、参与及支持行为分析——以秦岭地区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2):16-25.
[14] 王咏,陆林.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及应用——以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为例[J].地理学报,2014,69(10):1557-1574.
[15] 罗锐,许军.西南贫困地区山地户外运动资源开发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1):92-96.
[16] Liu Y,He J,Chen Q,et al.Mountain outdoor tourism and tibetan mountain guides’ place identity:the case of Mt.Siguniang Town[J].Sustainability,2022,14(22):14926.
[17] Burch Jr W R. The play world of cam**:Research into the social meaning of outdoor recre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5,70(5):604-612.
[18] 凌小盼,张位中,王冰,等.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山地户外旅游目的地“三生”空间构建路径研究(英文)[J].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1-10.
[19] 黄顺华.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期刊评价指标分类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21.
[20] 杜家菊,陈志伟.使用SPSS线性回归实现通径分析的方法[J].生物学通报,2010,45(2):4-6.
[21] 阿荣高娃,孙根年,乔少辉,等.内蒙古A级景区客流量估算模型——5个单因素方差分析与多元回归建模[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33(12):193-200.
[22] 蒋卓芮,刘东锋,姜大勇.跨越区域:北京冬奥会居民感知对凝聚力的影响——基于上海和沈阳非举办地样本的解释[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1,37(5):61-72.
[23] 吴蓉,施国庆.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经济精英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南京市Z村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4):53-62.
[24] 张宏梅,陆林.游客涉入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盎格鲁入境旅游者与国内旅游者的比较[J].地理学报,2010,65(12):1613-1623.
[25] 邹波.游客旅游意向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家,2021(7):40-45.
[26] 周学军,向林娟,雷彩霞.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37(12):172-181.
[27] 张立.现代性视域下的凉山彝族文化认同与文化权力研究[J].红河学院学报,2020,18(1):44-46.
[28] 王凯,陈勤昌,李志苗.遗产旅游地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感知的历时性研究——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J].应用生态学报,2018,29(3):997-1005.
[29] 韩磊,乔花芳,谢双玉,等.恩施州旅游扶贫村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J].资源科学,2019,41(2):381-393.
[30] 方德敏,杨钊.自然观光地旅游企业主移民地方感研究——以九寨沟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7,29(5):28-37.
[31] 段雨欣.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D].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20.
[32] 姚治国.旅游者对旅游生态标签认证的态度差异及影响因素[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41(5):8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