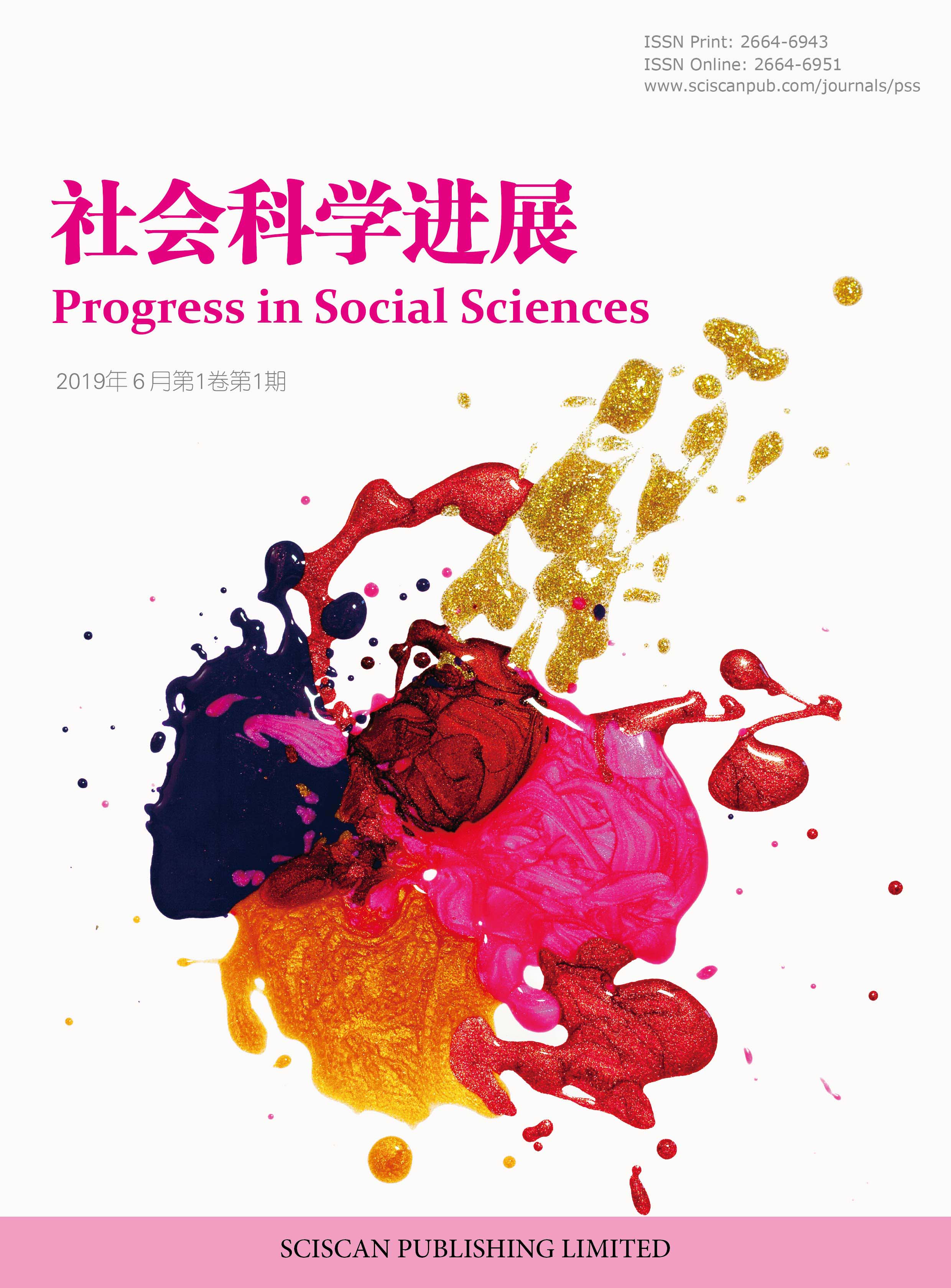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s
国际法院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适用研究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 Authors: 吴仪 黄怡婷
-
Information: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
Keywords: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udicial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可持续发展原则; 司法适用; 国际环境法
- Abstrac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s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thatemerged only in the 1970s. As a basic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law,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promoted by the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in the tri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cases, from the first use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GayBaskov - Rakimaro Dam case to the explicit formu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case, which hascontributed to the judicial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 has been facilitated. However, the ambiguity of the principle itselfand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he principle of State sovereignty have led theICJ to adopt a very cautious and conservative approach to the application of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hortcoming can be improvedby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inciple itself and establishing a completeinstitutional system. 国际环境法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一个国际法分支。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国际法院在对国际环境案例的审判过程中,从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水坝案中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到乌拉圭河纸浆厂案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原则,都促进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司法适用。但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由于其原则自身的模糊性以及国家主权原则的限制,使得国际法院在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时采取了十分审慎保守的态度。可以通过明确原则本身的内涵和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来完善这一不足。
- DOI: https://doi.org/10.35534/pss.0506056
- Cite: 吴仪,黄怡婷.国际法院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适用研究[J].社会科学进展,2023,5(6):607-618.
随着国际环境法的不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很多条约明示或者暗示地承认可持续发展原则。但是可持续发展原则大多规定在一些宣言决议等的软法文件中,导致国际法院在适用可持续原则时,面临着内部制约和外部阻力。本文将从明确原则本身的内涵和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1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含义和要素
1.1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定义
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很多环境条约明示或默示地承认可持续发展原则。[1]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很广。当前国际环境法学界尚未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本内容形成统一认识。[2]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不能只看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要注重开源节流,保障后辈子孙对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它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要控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以承载的范围之内,又不能使发展处于停滞状态。[3]
1.2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要素
“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内容是要求经济的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4]可持续发展原则包括四个内容,即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和发展一体化。
1.2.1 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由三项基本原则组成。保存选择原则。每一代人应该为后代人保存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以避免不适当地限制后代人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满足他们的价值时可得到的各种选择,又享有拥有与他们前代人较为多样的选择;保存质量原则,即每一代人应该保持地球的生态环境质量以便使它不会从前代人手里接下更坏的状况传递给下一代人,可以享有前代人所享有的那种行星质量的权利;保存取得和利用原则,即每一代人应对其成员提供平等的取得和利用前代人遗产的权利,并为后代人保存这项取得和利用权。
1.2.2 代内公平
代内公平则是指代内的所有人,无论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对于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享有平等的权利。[5]
1.2.3 可持续利用
可持续利用是指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是对资源利用的“度”的把握,即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要适应自然的再生和承载能力。对于可再生资源,要在保持其最佳再生能力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对于不可再生资源,要以不至于使其耗尽的方式利用,避免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有度地利用自然资源,一方面使它发挥最大的效益,一方面又不损害它的再生和永续能力。
1.2.4 环境与发展一体化
环境与发展一体化是指将保护环境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一方面要求制定经济和其他发展计划是切实考虑保护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在追求保护环境的目标时充分考虑发展的需要。
2 国际法院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适用——以案例为切入点
国际法院的基本文件、规约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法院主要受理的案件有领土、边界纠纷,以及国家间的环境的争端。
2.1 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
国际法院裁决的首例国际环境法案件主要是围绕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关于多瑙河盖巴斯科夫水坝的争端展开。1977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布达佩斯条约》,两国决定在多瑙河建设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水利系统。随后双方因为经济原因,放慢了水电站的建设速度,于是双方签署协议决定推迟至完工,同时对工程进行了调整。1989年出于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的一系列担忧,匈牙利政府认为多瑙河的生态利益高于水利项目的生态利益,因此匈牙利政府于10月27日正式决定终止该项目所有建设。但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在年初已经完成了主体工程建。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进行磋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A~G七种代替方案,但匈牙利认为这些方案都会影响到自然环境进而违反《布达佩斯条约》中第15、19和20条关于保护环境的义务以及相关条约和一般国际法。随后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决定实施“临时解决方案”继续建设该项目,并将多瑙河水截引至其领土上。1993年,双方将分歧提交国际法院裁决。[6]
国际法院就双方当事国提交的事项作出裁定。国际法院认可该因为生态抗辩有关责任的合法性,但否认匈牙利关于该项目具有严重而紧迫的生态危险的主张,进而认为匈牙利无权中止1977年条约;该条约仍然有效,捷克斯洛伐克单方面控制共享资源,剥夺了匈牙利公平合理适用多瑙河自然资源的权利,违反了国际法关于反制措施必须和所遭受的损害相称的要求,它无权从1992年10月起将“临时解决方案”投入运行,两国需要进行诚意的谈判,采取措施保证经双方同意修改的《布达佩斯条约》的目标的实现,两国必须根据该条约制定一个联合运营的方案;两国必须互相赔偿因各自违约造成的损失。
国际法院在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水坝案的案情争端裁决中接受和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这是国际法院第一次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给予了司法承认,“这种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必要性,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中得到适当的表达”。国际法院还明确提到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利益等相关概念。当时的卫拉曼特雷法官在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个别意见书中指出:“发展的权利和环境保护的权利是目前构成国际法主体一部分的原则。它们可能会相互冲突,除非由一个国际法原则指出它们应该如何协调,即可持续发展原则。”根据他的意见,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当代国际法的原则。[7]
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得出:(1)“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法律约束力,从国际法院表达来看,此处的“概念”具有“原则”特征,即被认为是统摄、解释和发展各种具体法律规则的指引;(2)“可持续发展”概念对于条约解释具有参考意义;(3)它是一项辅助规范或者概念工具,用来证明未经过严密法律推理和论证的创新结论的合理性。[8]
2.2 确立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司法承认
在继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水坝案国际法院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后,国际法院在裁判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明确使用“可持续发展原则”。1975年,乌拉圭和阿根廷签署了《乌拉圭河规约》,明确了两国关于结合乌拉圭河的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规定由双方共同建立乌拉圭河管理委员会负责规约的具体实施。2003年起,乌拉圭先后批准了两家外资企业在乌拉圭河本国沿岸一侧建设纸浆厂。这一行为引起了阿根廷政府和相关环保团体的强烈抗议,但该纸浆厂历史上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获得了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融资。对于乌拉圭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都有重大意义。两国多次协调,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阿根廷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乌拉圭单方面授权建设和运营纸浆厂及其相关设施是否违反边界河流利用和保护的程序性义务和实质性义务,即是否违反《乌拉圭河规约》的事先通知与协商等合作义务,进而损害了阿根廷的环境利益。国际法院基于两国之间的双边条约对争议焦点作出了分析。在程序性义务方面,国际法院指出,事先通知和协商义务是双方合作判断拟定工程的环境影响、消除或减少损害风险的基础,是双方利用乌拉圭河时必须善意遵守的义务。国际法院认为,乌拉圭在对两个纸浆厂的港口码头发布初步环境许可之前,没有将开展计划的工程告诉相关委员会和阿根廷。这一行为违反了《乌拉圭河规约》第7条至12条有关合作机制的程序性义务。在实质性义务方面,法院认为该纸浆厂没有给乌拉圭河造成实际污染,因此没有违反规约所规定的实质性义务。对于程序性义务的违反,宣布不法行为即可。
国际法院认为,公正合理利用共享资源和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所在。边界河流的开发利用应该考虑对河流环境和沿岸国家经济发展权利的持续保护,在不违反环境保护义务的前提下,国家拥有发展经济的正当权利,应当以此对乌拉圭批准建造和运营纸浆厂的行为进行评估。这就使得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国际环境纠纷的当事国有了法律约束。对比在1997年的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水坝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可持续发展“概念”与“原则”已经可以互换使用。第二,明确将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条约解释原则,并贯穿条约的目的、具体条文的内容和词语的涵义的解释的始终,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实质上影响了争议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对裁决结果有直接影响。第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开始影响裁决案件的核心国际法规范,作为高层次的指导性原则整合涉及共享水资源保护的各领域国际法的效果得以增强。第四,将环境影响评价确定为一项习惯国际法义务,尤其是在共享资源利用领域。
2.3 丰富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司法实践
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在圣胡安河归属问题上存在长期争端。两国曾在1858 年签署边界条约。2010年10月18日,尼加拉瓜开始疏浚圣胡安河以改善其适航性,同时在波蒂略岛北部地区进行建筑施工。2010年11月18日,哥斯达黎加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称尼加拉瓜侵犯并占领哥斯达黎加领土,正在和计划进行的疏浚和兴建运河工程将严重影响进入哥斯达黎加科罗拉多河的水流,并会进一步损害哥斯达黎加领土,包括位于该地区的一些湿地和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同年,哥斯达黎加开始建造公路,该工程位于哥斯达黎加境内经过尼加拉瓜部分边界地区。尼加拉瓜也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哥斯达黎加在两国边界和拉姆萨尔保护湿地附近修建道路侵犯了尼加拉瓜主权,并对其领土造成重大环境损害。
国际法院就这两个合并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当事双方的专家作证。最终,法院以全票通过,哥斯达黎加违反了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法庭认为,哥斯达黎加未能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目前不会对尼加拉瓜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可能进一步影响它们,没有理由批准尼加拉瓜所要求的停止继续采取行为的补救办法。且法庭认为恢复原状和赔偿是对物质损害的赔偿形式,虽然哥斯达黎加没有遵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但尚未确定道路的建设对尼加拉瓜造成重大损害或违反国际法规定的其他实质性义务。
本案中国际法院确认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一般国际法地位。明确了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前提,即活动具有产生重大跨界环境损害的风险,且是否存在这种风险由拟采取行动的国家基于对所有相关情况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具体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由一国在其国内法或授权该活动时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决定,但国内法对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不能免除一国在一般国际法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环境影响评价应在活动开始前即做出,且该义务在活动进行的全过程中是持续存在的。[9]
3 国际法院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存在的问题
1992年《里约宣言》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了一项国际法原则。但是1997年国际法院在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案才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直到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才承认了“可持续发展原则”。
3.1 可持续发展原则模糊性的制约
国际法院在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比较谨慎保守的,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国际法院尊重国家主权原则是密不可分的。
3.1.1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模糊,使得可持续发展原则难以作为判案的实质标准。因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虽然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但是它的内涵仍然处在发展中,呈现出动态的特点,从最初的限定为防止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发展到开始关注当代需要和后代需要之间的平衡,强调环境保护是全球责任,并且不仅是当代乃至后代的责任,并且囊括消除贫困、促进持续和公平发展等要素,综合讨论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因素的合理平衡。如此不确定的内涵,直接导致了各国在实践中的争议,国际法院也不能以司法裁决的方式具体定义。
3.1.2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法律地位存在争议
由于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在缺乏最高权威机构的情况下,考虑到国际社会政治文化的多样性,要想使新的规则获得广泛同意,无论是通过国际谈判还是形成一些习惯,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而“软法”却相对更为容易达成,国际环境法中的大量的规范也属于这种性质,这也影响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地位的确定,既不是一般法律原则,也不是习惯法原则,其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国际法院的适用过程中,会避免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使得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实际约束力被减弱。因此,可持续原则的法律地位的确立需要国际环境法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家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深入。
3.2 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制约
主权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从国际争端的提交到最后裁决的执行,都由国家意志决定,这也会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司法适用造成一定阻碍。
3.2.1 国家选择司法解决环境争端的意愿不足
司法作用的发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国际司法机构的求助,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希望将国际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尽管国际法院的审理过程十分的稳定明确并且公开透明,但是它只是争端解决的方式之一。有关国际环境法领域中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争端,这个领域相关的规则都处在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这使得国家将争端提交给国际法院会面临着很多不确定的法律风险,国际法院的约束力一直持续到判决的执行,这就使得国家不愿意将争端提交到法律手段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国际法院。而且国际法院从提交争端到做出判决需要一定的时间,其解决争端的效率远远不如外交和政治手段。
3.2.2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实质标准的制定权在国家
可持续发展原则虽然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但是并不存在统一的、明确的行为标准。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各国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理解不同,其具体的行为模式也不同:世界银行支持弱的可持续性,而环境主义者和生态经济学家支持强的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都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来采纳。这种理解的不同,使得实践中有关资源利用、动植物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标准也存在着差异,国际社会没有达成权威一致的标准。
如何评估目前的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问题,即要设置何种指标来表现和评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和程度是赋予可持续发展具有操作性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些标准和指标的设置权利仍然在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原则仍存在不同的态度,基于不同立场而持对立的见解,难以确定统一的标准。这会使得法官在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时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国际司法机构不是立法机关,不能代替国家确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的标准,只能将实质标准的决定权交给国家,尽量促进国际合作。
4 关于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完善建议
针对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完善。
4.1 明确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涵
明确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涵并且将可持续发展原则落实到具体制度中,从制度层面上来完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适用,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国际合作制度、跨界污染损害责任制度等。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要求在进行各种规划、开展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时对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效地统一起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10]
国际环境法中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目的是一方面推动各国实施国内环境影响评价,另一方面在于促进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有关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公约大多是框架性的,仅仅规定了一些原则性内容,其中的具体实施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为了确保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确定性,需要通过国际和国内法对相关内容作出具体规定。首先,可以通过对拟建项目的性质、规模、位置的具体限定来确定需要实施跨界影响评价活动的项目范围。其次,对于“重点不利跨界影响”需要以具体的数据来更加直观化地呈现。最后,明确起源国对潜在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的通知义务,并且对国家协商的程序以及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应包括的内容都做出具体规定,并将最后做出的决议告知受影响国。
推进清洁生产制度,政府应该从服务和引导的角度引发,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政府应该结合各行业的不同特点通过制定清洁生产指南,使之具有可操作性。第二,政府一方面要编制各行业的清洁生产审计规范,明确清洁生产审计的范围、内容、方法、途径和程序;另一方面要注意培育一批清洁生产审计的服务机构,为需要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和单位提供服务,指导如何开展清洁生产工作。第三,注意对清洁生产的示范建设。对清洁生产制度落实得较好的企业,进行政策鼓励和激励,利用媒体力量加强宣传。
国际合作制度是指世界各国本着友好协商,相互合作,对全球环境问题方面采取必要的共同行动和措施的制度。环境污染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因此,建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制度,世界各国为保护环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成为应对全球环境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国际社会可以在以下方面不断努力:完善国际环境法律体系,推动全球环境保护法制化;完善通知、协商和环境信息的交流制度;发展区域环境合作机制;技术合作与援助;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机构。
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完善跨界污染损害责任机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第一,以预防为主,完善环境污染预防机制。实施这项机制首先应该对一国的活动进行评估,判断出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从而提前采取措施进行有效预防,进一步明确责任的归属和承担。第二,针对污染时间所引发的责任,行为国应当予以承担。很多国家条约中强调在污染波及其他国家的时候,行为国负有及时告知他国的义务和责任。第三,弥补损害责任的发生,需要加大资金方面的补偿,这就需要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
4.2 建立完整的制度体系
可持续发展原则虽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决议和宣言等文件中都得到反映,但是很多领域都没有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强制规定使其从价值观念变为基本原则,有的领域已经有相关法律文件加以调整但是缺少约束力,或者相关公约的规定大多是框架性的,还需要成员国通过多边、双边协商来解决具体问题。原则的核心功能是确定责任分配,作为基本原则应当通过各种法律文件将其落实到相应的主题上成为具体的制度或措施。而且该原则相关法律法规比较零散,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缺少强有力的管理监督机构,这也使很多不愿承担义务的国家有借口规避责任。
因此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将该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并付诸实践是实现该原则的根本保障,比如在国内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就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思想;再比如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是通过预防污染避免走非可持续道路。可持续发展原则除了制度层面的落实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层面来解决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适用问题。[11]在体系化条约的基础之上,建立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司法标准,促进国家选择将有关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处理。
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的原则,不仅丰富了国际环境法的内容,同时,国际环境法的有效实施也离不开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国际环境法实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国际环境法的最终目的。通过国际法院审理环境案件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适用,使得可持续发展原则得到司法确认。但是也需要看到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原则自身概念和司法地位的模糊,针对这一不足,我们主要是通过法律的编纂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进一步落实。
参考文献
[1] 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编.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汇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2] 王曦.论国际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J].法学评论,1998(3):73-78.
[3] 高桂林,杨雪婧.生态文明视野下自然资源法治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
[4] 林灿玲.国际环境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王曦.论国际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J].法学评论,1998(3):73-78.
[6] 史学瀛.环境法案例教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
[7] 卢锟.国际法院对国际环境法原则的司法适用[J].人民法治,2018(4):32-35.
[8] 罗念.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演进研究——以国际司法适用为中心的考察[J].环境资源法论丛,2015,10(00):140-183.
[9] 蹇潇.哥斯达黎加境内圣胡安河沿岸的道路修建案法律评论[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3):88-92.
[10] 王立业.论国际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D].中国政法大学,2007.
[11] 彭亚媛,马忠法.《世界环境公约(草案)》制度创新及中国应对[J].太平洋学报,2020,28(5):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