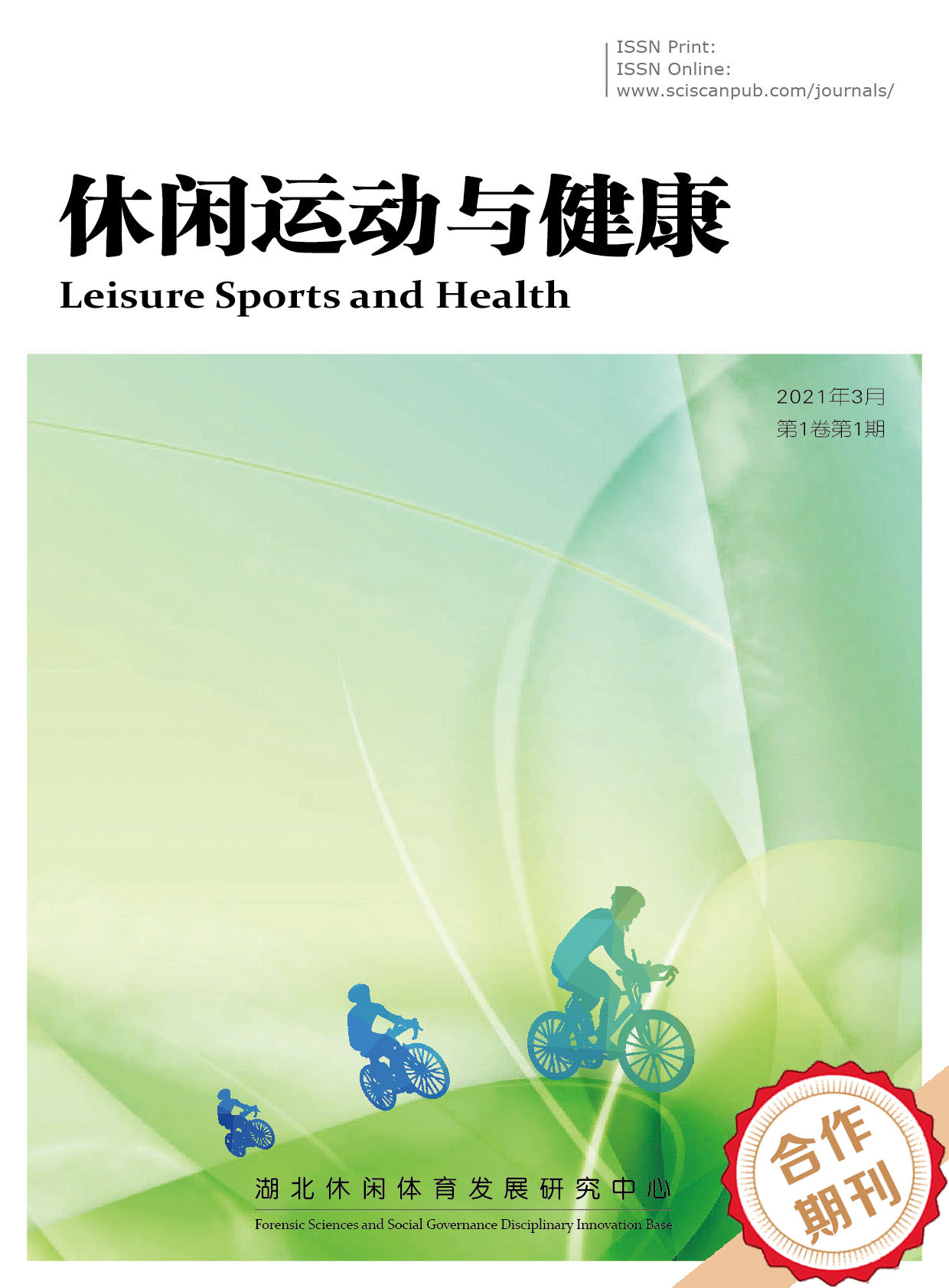Leisure Sports and Health
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运动员线性速度影响的元分析
Effect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Sprint of Athletes: A Meta Analysis
- Authors: 李西金 刘仕彬 阮香君 李斌
-
Information: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
Keywords:
Plyometric training; Athletes; Sprint; Meta-analysis快速伸缩复合训练; 运动员; 线性速度; 元分析
-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sprint,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lyometric training practice.Method: With CNKI, web of science and PubMed as the literature sources, the retrieval date is from January 1, 2000 to September 1, 2020, to search for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 about the influence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sprinter performance. The PEDro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literature, and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CMA3.0 software was used for metaanalysis. Result: Plyometric train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print performance of athletes(ES=-0.803,95%CI [-0.98,-0.626], P<0.001)Through the subgroup analysis of sprint performance, the plyometric training program of long-term (>8 weeks), sessions (>16 sessions) and 3 times / week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other sports programs; meanwhile, the source country of literature and gender may be the source of heterogeneity. Conclusion: Plyometric training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athletes’ linear speed. Its practic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pecificity and select training methods for special projects. 目的:本文旨在探究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运动员线性速度的影响,为未来研究及练时间提供依据。方法:检索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PubMed 数据库中相关文献,检索日期为2000 年至2020 年8 月1 日,搜集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运动员线性速度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通过PEDro 量表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估,应用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CMA3.0 软件进行元分析。结果:快速伸缩复合训练与抗阻训练或一般替代训练相比较,对提高运动员线性速度具有更高的训练效益(ES=-0.803,95% CI[-0.98,-0.626],p<0.001)。调节效应检验显示长期(>8 周)、多课次(>16 总课次)、3 次/ 周的训练计划显著优于其他运动方案。结论:快速伸缩复 合训练是提高运动员线性速度的有效方法,其实践应遵循特异性原则,针对专项特点,选择训练手段。
- DOI: https://doi.org/10.35534/lsh.0104007 (registering DOI)
- Cite: 李西金,刘仕彬,阮香君,等.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运动员线性速度影响的元分析[J].休闲运动与健康,2021,1(4):35-41.
运动员的反应力量水平决定了专项成绩的高低[1],反应力量是指肌肉完成拉长-缩短周期(Stretch-shorting Cycle)时表现出的力量[2],它的机制是人体进行跑、跳、投等动作时,由于骨骼肌受到周期性冲击或拉力的作用,肌肉先进行离心收缩,紧接着进行向心收缩,这种离心和向心的结合,构成了肌肉活动的一种自然形式[3]。在以SSC运动为基础的实际训练中,快速伸缩复合训练(Plyometric Training,PT)作为典型的SSC运动的训练手段,已被普及和应用到运动员的爆发力训练计划之中,它的首要目的是旨在通过各种跳跃训练,增强肌肉功能[3]。
多项研究证实快速伸缩复合训练是适用于所有体育项目的一种提高成年及青少年力量[4,5]、速度[6,7]、灵敏[8,9]、跳跃[10,11]等能力的训练方法。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如何有助于提高加速跑能力的机制尚未明确,根据Markovic和Mikulic的观点[12],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增强了神经系统和肌腱系统在最短时间内产生最大力量的能力,并认为以拉长-缩短周期为机制的训练手段是提高力量和速度之间的桥梁。与抗阻力量训练相比较,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可诱发特定的神经适应,例如增加运动单元的激活以及减少肌肉肥大[13]。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在运动康复中也得到了有效实施[14],它的应用重点是提高下肢肌肉控制能力以及正确的运动机制,并逐渐向高强度的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发展,为骨骼-肌肉系统的快速运动以及运动中所需的高强度力量做好准备。
本研究使用元分析方法,综合量化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运动员线性速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影响训练效果的干预方案,为未来研究提供量化证据。
1 方法
1.1 文献筛选
由第一作者对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Medline 3个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间2000年至2020年9月1日所有公开表表的文献,对3组关键词进行组合检索:①Plyometric training、Plyometrics、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增强式训练、跳深训练;②Sprint、短跑;③Athlete、运动员。将所有纳入文献导入到文献管理软件EndNote X8。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原始研究的纳入遵循循证医学PICOS的方法,主要考虑研究设计(Study Design)、干预措施(Interventions)、参与者(Participants)、对照组(Comparisons)、研究结果(Outcomes)5个因素。纳入标准:①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RCT);②干预组必须是独立的快速伸缩复合训练;③干预对象为运动员;④各指标无基线差异;⑤实验结果至少包括一项短跑测试结果,且统计量的均值、标准差、样本量(n)描述清晰的文献。排除标准:①不满足任何一条纳入标准的文献;②没有全文或综述类文献。
基于纳入与排除标准,符合要求的文献为12篇(见图1)。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1.3 文献质量评估
研究质量的评价是评估单个研究在设计、实施和分析过程中,防止或减少偏移或系统误差的情况,也称为方法质量学评价(Assessment of Quality)。本研究采用PEDro(Phsiotherapy Evidence Database,物理治疗证据数据库)量表。PEDro量表由11个题目组成,除了首题不计分外,其余每题计1分,共10分,总分小于或等于3 分,文献的研究质量较低,4-5 分为中等质量,6-10 分为高质量。
1.4 数据提取及编码
使用Excel进行原始研究的数据录入,为了保证数据提取及编码的准确性,本研究数据处理工作由3名研究生共同完成。研究员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章,任何灰色区域都会提交并与第二研究员进行讨论,任何分歧都会由第三研究员仲裁。文章首先按标题筛选,然后按摘要筛选,最后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全文筛选。需要编码的信息是:文章作者、发表年份、干预对象、干预方案(周期、频率)等。
1.5 数据分析
效应量的计算具体是使用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CMA 3.0)软件,它是将若干个同类研究的结果合并为一个效应量。根据统计学原理,纳入元分析的原始研究来自不同年份、地区,研究对象、样本量也不尽相同,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我们将系统评价中不同研究的差异统称为异质性[15]。检验异质性是为了确定研究间是否异质,进一步选定数据分析模型。检验方法主要是Q检验和I2检验,Q检验是基于总变异的检验,假设效应量服从卡方分布,如果p<0.05,则说明研究间存在异质性;I2检验主要呈现了效应量的真实变异在总变异中所占比重,I2>50%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
合并效应量是将若干个同类研究的结果合并为同一个效应量。本研究的数据资料属于连续性数据,由于选取了不同的结局指标(5m、10m、15m、20m、30m、60m、100m),所以采用了标准均差(Standard Mean Difference,SMD)和95%置信区间(95%CI)作为效应尺度进行合并效应量(Effect Size,ES),合并效应量小于0.2为微效应,在0.2-0.5之间为小效应,在0.51-0.8之间为中等效应,合并效应量大于0.8为大效应[11]。
1.6 发表偏误
通常,在学术期刊论文中,具有显著性的统计结果更易接受和发表,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发表偏倚的问题。偏倚又称系统误差,是指研究的结果或推论偏离真实值,或导致这种偏离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在资料的收集、分析、解释或发表过程中,能够导致结论系统地与真实值有所不同的任何趋势[16]。首先,我们在文献获取阶段就尽可能搜集符合标准的文献,其次是使用漏斗图、Egger’s法和Begg法三种方法进一步检验发表偏误。
2 结果
2.1 研究特征
纳入研究的12篇文献,如表1所示,其中外文文献7篇,来自期刊文章;国内文献5篇,均来自硕士论文。共包括341名18-24岁的中外运动员,年龄跨度较小;均为现役运动员,运动项目涉及篮球、排球、足球、橄榄球、板球、短跑、长跑7个运动项目。
所纳入的 12项研究文献的 PEDro 得分,如表2所示,7分1篇,5分文献9篇,4分文献2篇,平均得分5分,为中等质量。值得注意的是仅有一篇文献获得了高质量评分(≥6分),它的实验设计采用了分配方式隐藏以及受试者设盲,严格来说,双盲RCT(随机对照试验)是最可靠的研究,但是由于现实问题,在训练干预期间很难对干预对象和实施干预的教练员全部设盲。因此,不同原始研究实验设计的差异,可能导致偏误的情况。
表 1 纳入文献特征一览表
| 研究作者 | 国家 | 干预对象 | 样本量 | 性别 | 年龄 | 身高/cm | 体重/kg | 周期/周 | 频率次/周 |
| Houghton | 澳大利亚 | 板球运动员 | TG:7 | M | 21 | 174.6 | 73.68 | 8 | |
| CG:8 | M | 21 | 179.3 | 78.53 | 8 | ||||
| Ozbar | 土耳其 | 足球运动员 | TG:9 | F | 18.3 | 163.1 | 58.8 | 8 | 1 |
| CG:9 | F | 18 | 159.1 | 54.4 | 8 | ||||
| Ozbar | 土耳其 | 足球运动员 | TG:10 | F | 19.4 | 163.6 | 58 | 10 | 2 |
| CG:10 | F | 19.1 | 163.1 | 55.3 | 10 | 2 | |||
| Ramirez | 智利 | 长跑运动员 | TG:17 | F、M | 22.1 | 59.8 | 6 | 2 | |
| CG:15 | F、M | 6 | 2 | ||||||
| Ramirez | 智利 | 足球运动员 | FTG:19 | F | 22.4 | 159 | 60.2 | 6 | 2 |
| FCG:19 | F | 20.5 | 161 | 60.7 | 6 | 2 | |||
| MTG:21 | M | 20.4 | 174 | 71.5 | 6 | 2 | |||
| MCG:21 | M | 20.8 | 171 | 68.4 | 6 | 2 | |||
| Rimmer | 新西兰 | 橄榄球运动员 | TG:10 | M | 24 | 177 | 83 | 8 | 2 |
| CG:9 | M | 8 | 2 | ||||||
| Yanci | 西班牙 | 足球运动员 | TG1D:12 | M | 22.5 | 69.3 | 170 | 8 | 1 |
| TG2D:15 | M | 8 | 2 | ||||||
| CG:12 | M | 8 | 2 | ||||||
| 姚文翔 | 中国 | 短跑运动员 | TG:6 | M | 19.3 | 178.5 | 68.3 | 12 | 4 |
| CG:6 | M | 19.5 | 179.6 | 65.8 | 12 | 4 | |||
| 徐良医 | 中国 | 短跑运动员 | TG1:6 | M | 19.8 | 176.5 | 72.2 | 8 | 3 |
| TG2:6 | M | 8 | 3 | ||||||
| CG: | M | 8 | 3 | ||||||
| 李宁 | 中国 | 篮球运动员 | TG:12 | M | 20.7 | 185.9 | 79.8 | 12 | 3 |
| CG:12 | M | 12 | 3 | ||||||
| 李宁 | 中国 | 短跑运动员 | TG:12 | M | 19.6 | 176 | 68.4 | 8 | 3 |
| CG:12 | M | 20 | 175.9 | 70.6 | 8 | 3 | |||
| 王欢 | 中国 | 排球运动员 | TG:12 | F | 19.7 | 179.6 | 67.4 | 8 | 2 |
| CG:10 | F | 19.4 | 179.7 | 67.6 | 8 | 2 |
注:M:男性;F:女性;TG:实验组;CG:控制组。
表 2 文献质量评估
| 作者及年份 | 说明受试者纳入条件 | 随机分配受试 | 分配方式隐藏 | 基线相似1 | 受试者设盲2 | 教练员设盲2 | 评定者设盲2 | 对85%以上的人进行至少一项主要结果的测量3 | “意向治疗分析”4 | 组间统计报告 | 结果的点测量值和变异测量值 | PEDro得分 |
| Houghton2013 | 1 | 0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4 |
| Ozbar2014 | 1 | 1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5 |
| Ozbar2015 | 1 | 0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4 |
| Ramirez2014 | 1 | 1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5 |
| Ramirez2016 | 1 | 1 | 1 | 1 | 1 | 0 | 0 | 1 | 0 | 1 | 1 | 7 |
| Rimmer2000 | 1 | 1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5 |
| Yanci2017 | 1 | 1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5 |
| 姚文翔2018 | 1 | 1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5 |
| 徐良医2019 | 1 | 1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5 |
| 李宁2017 | 1 | 1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5 |
| 李宁2019 | 1 | 1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5 |
| 王欢2019 | 1 | 1 | 0 | 1 | 0 | 0 | 0 | 1 | 0 | 1 | 1 | 5 |
注:1就最重要的预后指标而言,各组在基线都是相似的,2实施盲法,3如果未报告则按照负向结果采纳,4所有被试均按照要求完成试验和测试,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应对至少有一项主要结果进行,如果没有报告则按照负向结果采纳
2.2 发表偏误
漏斗图法是测量发表偏移中常用的可视化方法,是以单个研究的效应量作为X轴,每个研究的样本大小为Y轴,做出的相应的散点图。由图2可知,纳入研究的12篇文献的26个效应量均匀分布在效应量平均值两侧,Egger’s线性回归法检测结果t=0.81,p=0.21>0.05,Begg秩相关法检验结果Z=1.72(p>0.05),发表偏误结果均显示无明显发表偏误。

图 2 漏斗图
2.3 Meta分析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Q=47.021,p<0.001,I2=46.83%,存在中度异质性;I2值<50%,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12篇文献的26项研究中,共326人比较了快速伸缩复合训练与对照组线性速度的差异。合并效应量结果显示ES=-0.803,95%置信区间为[-0.98,-0.626],p<0.05,表明快速伸缩复合训练与抗阻训练或一般替代训练相比较,快速伸缩复合训练能够显著提高运动员线性速度。(见图3)

图 3 PT对运动员线性速度的影响
2.4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方法是用于评价某个meta分析或系统评价结果是否稳定和可靠的分析方法,通过改变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如:研究质量的高低、排除样本大小的极端值或是选用不同的效应模型等,重新进行Meta分析后与未改变条件之前的结果进行对比,若改变条件前后结果没有发生本质上的逆转,那么,则说明此次分析结果稳健性较好。本研究通过逐一剔除的方式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剔除前后效应量差异较小,且未本质改变效应量结果,证明此次Meta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较好。
2.5 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纳入文献的训练方案,凭据统计学因素,将不同干预周期划分为≤8周(短期)、>8周(长期),不同总训练课次划分为≤16次和>16次,干预频率划分为2次/周、3次/周。如表3所示。
表3 调节变量检验结果
| 研究特征 | 研究数量 | ES[95%CI] | I2(%) | p值 |
| 干预周期 | ||||
| ≤8周 | 19 | -0.66[-0.857,-0.463] | 44.54 | 0.019 |
| >8周 | 7 | -1.339[-1.802,-0.997] | 0 | 0.66 |
| 总课次 | ||||
| ≤16次 | 9 | -0.6[-0.867,-0.333] | 66.45 | 0.002 |
| >16次 | 9 | -1.091[[-1.409,-0.773] | 28.48 | 0.191 |
| 训练频率 | ||||
| 2次/周 | 13 | -0.767[-1.0,-0.533] | 60.86 | 0.002 |
| 3次/周 | 6 | -0.962[-1.348,-0.577] | 47.87 | 0.088 |
1)干预周次。短期训练的合并效应量ES=-0.66,95%CI[-0.857,-0.463],p<0.001;长期训练后的合并效应量ES=-1.399,95%CI[-1.802,-0.997],p<0.001,两者均有显著性差异,结果提示长期训练计划对运动员线性速度提高效果更明显。
2)总课次。将不同课次划分为总课次≤16次和>16次,总课次≤16次的合并效应量ES=-0.6,95%CI[-0.867,-0.333],p<0.0001,有显著性差异;总课次>16次的合并数据效应量ES=-1.091,95%CI[-1.409,-0.773],p<0.0001,有显著性差异;结果提示较多课次的训练计划对运运动员线性速度提高效果更显著。
3)训练频率。2次/周运动计划的合并数据效应量ES=-767,95%CI[-1.0,-0.533],p<0.0001,有显著性差异;3次/周运动计划的综合效应量ES=-0.962,95%CI[-1.348,-0.577],p<0.0001,有显著性差异;结果提示3次/周训练计划对运动员短跑成绩的提高更显著。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在显著的样本量(n=341)基础上,定量分析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运动员线性速度的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本次元分析具有中度异质性(Q=47.021,p<0.001,I2=46.83%),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逐一剔除文献前后异质性改变不明显,且未本质改变元分析结果,研究认为此次元分析结果稳健可靠,因此并未进一步探讨异质性的来源。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快速伸缩复合训练能够显著提高运动员线性速度(ES=0.-0.803,95%CI[-0.98,-0.626],P<0.001)。国外关于快速伸缩复合训练的Meta分析也同样证实了对提高线性速度的积极影响。Oxfeldt[17]等对25项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健康成人跳跃、速度、下肢肌肉力量的影响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短跑速度具有中等效应(ES=-0.59,95%CI[-1.01,-0.17],P=0.006)的积极影响。此外,Villarreal[18]等人对健康成人短跑速度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纳入26项研究),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包括结合负重训练、电刺激训练的复合训练对100米以内的线性速度具有小效应的积极影响。
干预方案是影响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运动员线性速度提高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次元分析为此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干预周期、频率以及总的训练课次是优化快速伸缩复合训练方案设计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结果显示,干预周期超过8周、3次/周的训练方案提高效果更明显。Villarreal[4]研究发现干预时间、频率和负荷与干预效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同时,3次/周的比2次/周的训练方案更有效,与本研究相互印证。总课次超过16次的方案比16课次及以下的方案更有效,moran[19]在青少年男性的研究中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因此,对于制定快速伸缩复合训练方案,建议干预8周及以上,总课次超过16次,3次/周的训练频率,以最大限度获得提高运动能力的训练效益。研究发现,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线性速度的提高可能是因为训练手段的特殊性。王欢[20]对高水平女排运动员进行8周、每周2次/周的训练干预后,对各项训练指标进行了评估,但结果未能显示出短跑成绩的提高,分析发现,其训练手段大多是垂直方向的快速伸缩复合训练。Dodd[21]认为与短跑成绩无关的跳跃练习(即垂直式跳跃练习)不会对短跑速度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一个包含更多训练手段的训练计划(例如,变向训练、负重训练),可能会比单一类型的练习获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目前的数据表明,快速伸缩复合训练是提高运动员线性速度的高效训练方法,它似乎特别适合需要高水平冲刺能力的运动,例如足球、篮球或田径,因此,它的应用应符合运动员的个人需求,并且要与运动员所从事运动的运动特点有关。也就是说,快速伸缩复合训练训练手段应反映该运动员从事运动中隐含的活动类型[22],即特异性原则。在许多运动和体育活动中都需要爆发式的速度,因此,除了众所周知的抗阻训练、抗阻专项训练、超速训练等提高线性速度的训练方法外,体能训练专业人士也可将快速伸缩复合训练纳入运动员的整体训练计划中,以达到高水平的腿部爆发力和积极的运动表现。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综合了各项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了较为有力的结论,但仍认识到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纳入原始研究少于3篇,对于某些结果如性别、训练课时间、从事项目等,没有进一步进行讨论,未来研究可在此展开深入研究;纳入文献实验设计中,仅一项研究涉及盲法,导致方法学质量不高;此外调节变量检验指标分类(干预周期、总课次)使用了中位数分割技术,可能存在残差混杂以及统计力低下[23]。
4 结论
快速伸缩复合训练与抗阻训练或一般替代训练相比较,能够显著提高运动员线性速度。>8周、>16总课次、3次/周的训练计划优于其他训练方案。其训练实践应遵循特异性原则,针对专项特点,选择训练手段。
参考文献
[1] 周彤,章碧玉,何梦梦.我国女子短跑后备人才下肢反应力量的研究[J].体育科学,2018,38(5):50-55.
[2] 陈小平.反应力量和反应力量的训练[J].体育科学,2001,21(5):36-39.
[3] 李志远,虞松坤,杨铁黎.肌肉“拉长—缩短周期”运动理论及其在爆发力训练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19,38(3):228-234.
[4] Saéz-Saez D V E,Eleftherios K,J K W,et al.Determining variables of plyometric training for improving vertical jump height performance:a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research,2009,23(2):495-506.
[5] Rodrigo R-C,Carlos H-O,Carlos B,et al.Effect of Progressive Volume-Based Overload During Plyometric Training on Explosive and Endurance Performance in Young Soccer Players[J].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research,2015,29(7):1884-1893.
[6] Goran M.Does plyometric training improve vertical jump height? A meta-analytical review[J].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2007,41(6):349-355.
[7] César M,Davide M.Effects of in-season plyometric training within soccer practice on explosive actions of young players[J].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research,2009,23(9):2605-2613.
[8] Miller M G,Herniman J J,MD Ricard,et al.The effects of a 6-week plyometric training program on agility[J].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 medicine,2006,5(3):459-465.
[9] Asadi A,Arazi H,Young W B,et al.The Effects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Change-of-Direction Ability:A Meta-Analysis[J].Abbas Asadi;Hamid Arazi;Warren B Young;Eduardo Sáez de Villarreal,2016,11(5):763-573.
[10] Makaruk H,Sacewicz T.Effects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Maximal Power Output and Jumping Ability[J].Human Movement,2010,11(1):29-36.
[11] Oxfeldt M,Overgaard K,Hvid L G,et al.Effects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jumping,sprint performance,and lower body muscle strength in healthy adult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es[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2019,29(10).
[12] Markovic G,Mikulic P.Neuro-Musculoskeletal and Performance Adaptations to Lower-Extremity Plyometric Training[J].Sports Medicine,2010,40(10):859-895.
[13] Slimani M,Chamari K,Miarka B,et al.Effects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Physical Fitness in Team Sport Athletes:A Systematic Review[J].Journal of Human Kinetics,2016,53(1).
[14] 孔令华,李令岭.神经肌肉训练对运动员ACL损伤康复与预防的研究综述[J].中国体育科技,2019,55(10):62-67.
[15] Higgins J P,Green S.Cochrane Handbook for Systematic Reviews of Interventions[J].Wiley-Blackwell,2008,
[16] 解超,金成吉,张军.有氧运动对我国肥胖少年儿童的干预效果研究——基于元分析方法[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0(2):84-90.
[17] Mikkel O,Kristian O,G H L,et al.Effects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jumping,sprint performance,and lower body muscle strength in healthy adult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es[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2019,29(10):1453-1465.
[18] Eduardo S,Requena B,Cronin J B.The effects of plyometric training on sprint performance:a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Strength & Conditioning Research,2012,26(2):575-584.
[19] J M,G S,C R M,et al.Variation in Responses to Sprint Training in Male Youth Athletes:A Meta-analysi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2017,38(1):552-565.
[20] 王欢.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对女排运动员移动速度的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2019.
[21] Dodd D J,Alvar B A.Analysis of acute explosive training modalities to improve lower-body power in baseball players[J].Journal of Strength & Conditioning Research,2007,21(4):1177-1182.
[22] DA Chu,Myer G D.Plyometrics[M].Human Kinetics,2013.
[23] Altman D G,Royston P.The cost of dichotomising continuous variables.BMJ 332:1080[J].Bmj,2006,332(7549):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