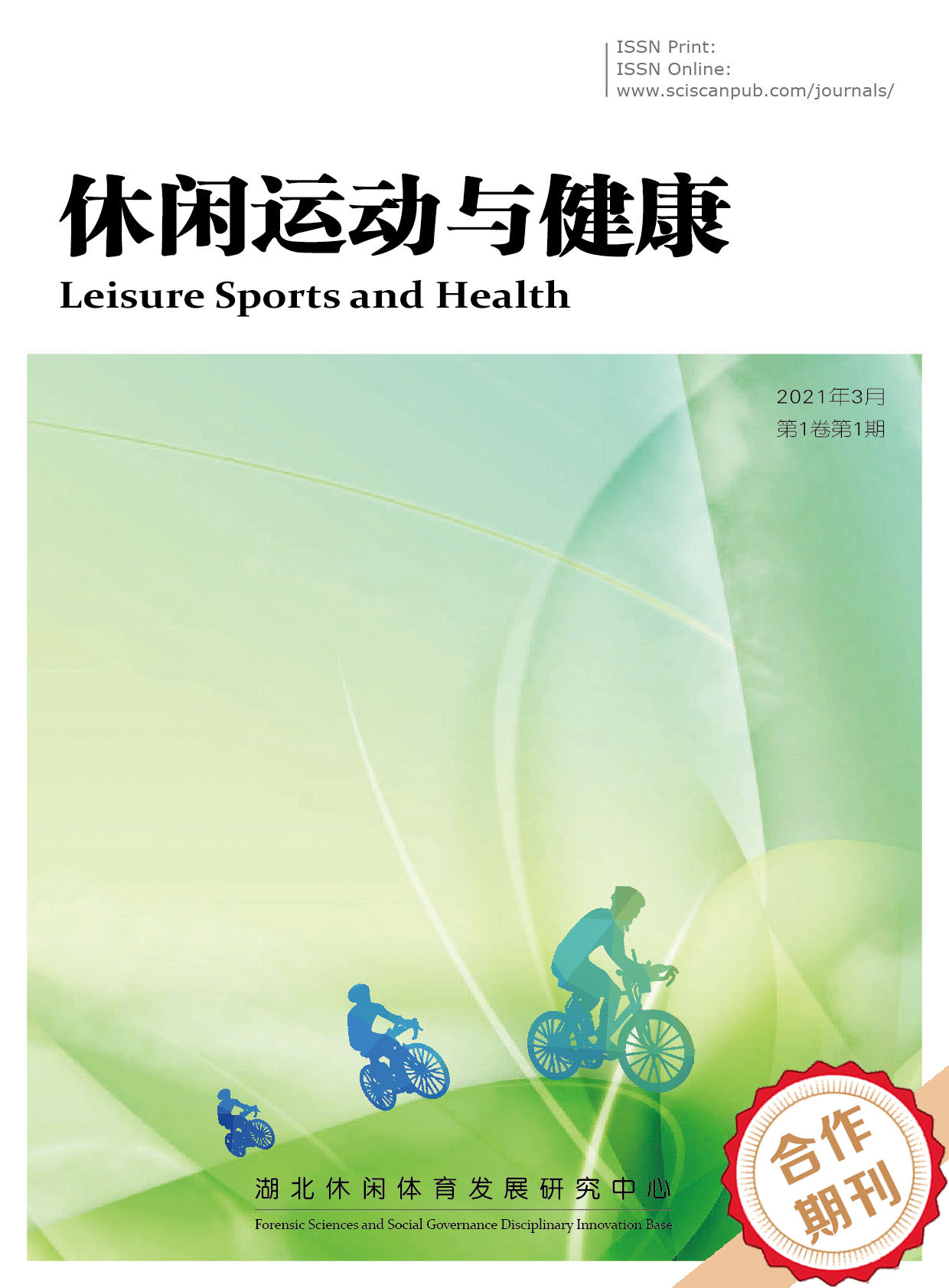Leisure Sports and Health
后疫情时期家庭体育发展策略研究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amily Sports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 Authors: 李婷
-
Information: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湖北武汉
-
Keywords:
Post-epidemic; Family sports; Sports resources; Coordinated governance后疫情; 家庭体育; 体育资源; 协调治理
-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family sports development, the author aims to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spor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current family sports environment is very lacking, the "family" "community" "school"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family sports development mode is a single one to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spor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sports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flexible use of physical training equipment,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sports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enrich the family sports development model, create a family sports environment, strengthen family sport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chool and family sports. 采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研究家庭体育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旨在为家庭体育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研究认为:当前家庭体育环境十分缺失;“家庭”“社区”“学校”三者协同治理能力不足;家庭体育开展模式单一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家庭体育的发展。因此,家庭体育的开展应采取如下措施;灵活运用体育锻炼设备;加强“互联网+”背景下家庭体育资源开发;丰富家庭体育开展模式,营造家庭体育环境;加强家庭体育宣传教育,推进社区、学校、家庭体育联合发展。
- DOI: (DOI application in progress)
- Cite: 李婷.后疫情时期家庭体育发展策略研究[J].休闲运动与健康,2021,1(2):69-73.
从新冠肺炎暴发至今,已持续了一年之久,疫情暴发势头迅猛,无论是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或体育产业的发展,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疫情期间,我国钟南山院士多次强调体育锻炼的作用,呼吁公众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可见体育锻炼对身心健康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是个体身体发育和体育锻炼的起点,更是培养习惯和助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摇篮”[1],家庭体育,是体育活动开展最基础的一环,然而目前,许多家庭都无法充分认识到它的作用,家庭体育的开展还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为此,对新冠肺炎背景下的家庭体育进行研究,为疫情后家庭体育的发展提供可行性参考。
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从政府、社会、个人(家庭)3个层面协同推进,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并规定到2022年,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到2030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健康公平基本实现。2019年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3]也提出到203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5%以上。通过上述文件可知,国家对体育与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体育锻炼所占生活比重会逐步增大。因此,在此趋势下家庭体育随之出现,也逐渐成为当下众多成员参与体育锻炼的方式。
1 关于家庭体育研究
1.1 国内关于家庭体育研究
王则珊认为家庭体育包括父母长辈在家庭中对儿童青少年的体育教育,家庭成员在家庭这一生存环境中进行的体育活动[4]。叶展红将家庭体育定义为是以家庭成员为活动对象,家庭居室及其周围环境为主要活动场所,根据居室环境条件与成员的需要与爱好,利用属于自己时间选择健身内容和方法,达到增进身心健康的目的,以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发展[5]。刘江南等人认为家庭体育是指以家庭成员为活动主体,为满足家庭成员自身的体育需求,以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家庭成员为单位而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体育活动,不介意其体育活动的地点是否在家庭内[6];张永保则把家庭体育作为以“家庭”为单位延展出来的体育活动,是一人或多人在家庭生活中安排的或自愿以家庭名义参与的,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获得运动知识技能、满足兴趣爱好、丰富生活、达到休闲娱乐、实现强身健体和促进家庭稳定为主要目的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7]。吴旭东提出家庭体育是指在家庭的安排下,以帮助儿童全面、熟练地掌握体育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运动能力、增强体质健康促进身心和谐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体育教育活动[8]。综上所述,家庭体育开展的对象主要是在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场所主要以家庭居室或是社区等周边环境为主,开展家庭体育的目的则以针对改善与促进家庭关系、利于身心健康、提升知识技能为主。
1.2 国外关于家庭体育研究
国外对家庭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家庭体育参与研究以及家庭体育模式研究。欧洲学者Jane E.[9]提出家庭结构、时间和体育参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学者Anna[10](2013)表示,在影像青少年儿童运动参与的众多因素中,家庭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德国家庭体育的开展中,主要有两种开展模式。第一,由家庭成员自主开展的家庭体育活动;第二,家庭成员参与体育俱乐部或体育协会开展的相关家庭体育活动。前者的管理实施与受益主体均是家庭,而后者由家庭和俱乐部共同形成统一的管理实施与受益主体。法国学者Åse Strandbu[11]通过研究表明了家庭体育文化与青少年自身体育参与具备一定的相关性。
2 家庭体育的重要性
2.1 家庭体育是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延伸
家庭体育作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父母的关注,家庭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三位一体发展已经成为现在体育教育的主旋律[12]。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场域,青少年对体育的最初认识及体育习惯的早期形成与家庭体育的开展密切相关;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二场域,青少年体育意识的培养及其运动技能的学习主要通过学校体育获得;社区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三场域,青少年体育习惯的保持与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状况和体育场地设施的完备情况密切相关[13]。目前学校与社区体育资源开发尚不能对家庭体育形成有力支持。仅仅依赖学校与社区的努力,青少年健康促进难以奏效,虽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体质健康,培养其锻炼意识,但它所带来的都是在某一范围内的锻炼效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回归到家庭本身,发展家庭体育,就正好可以弥补学校体育的空缺。家庭体育是幼儿接受体育教育的起点,它不仅为幼儿将来接受社区和学校体育打基础,还是伴随人一生的重要教育内容[14]。因此,家庭体育与学校和社区是在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彼此间协调制约,共同形成社会体育风貌。
2.2 家庭体育是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
家庭是青少年体育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促进青少年身体活动习惯中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体育后备人才的产生,不外乎有两个条件:先天基础以及后天的培养,后天的培养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体育。在家庭之中,家长具备的良好的体育锻炼意识,当家长积极参与各类体育项目活动时,也会给孩子造成一定影响,这便为未来优秀竞技运动员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开展家庭体育,培养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通过不同体育锻炼项目,促进其身体骨骼发育,使其协调性、柔韧性、平衡性均衡发展。因此,家庭体育的开展,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6]。
2.3 家庭体育是家庭建设的必要组成
众多研究表明,家庭体育的开展利于家庭成员身心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和谐关系的产生。家庭建设即精神文化建设与物质建设两个方面,精神文化建设,即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和谐的家庭关系。对于体育,也要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体育健身文化是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家庭和谐幸福的重要基础[17]。平等公正的教育方式以及和睦家庭的关系,对于孩子意识形成,提升家庭幸福度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幼儿时期,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其良好品格与行为的养成,绝大程度受到家长影响。父母对孩子的表现,也是将来孩子对其他人表现的映射。家庭体育是家庭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一座构建家长与孩子沟通的桥梁,通过开展体育项目,培养父母与孩子的协作能力,增强双方的沟通交流,加深相互间的情感,孩子所学到的坚持不懈与合作的精神,则是家庭文化的体现。
3 家庭体育开展现状
3.1 家庭体育发展的机遇
1)健康与体育锻炼意识的增强
疫情的到来,虽给许多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却使全民健康观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身体锻炼对健康的重要性。据统计,疫情期间运动健康类app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各类有氧无氧挑战活动、关于健身的网络直播等都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央频道也推出了系列关于体育锻炼的节目,这些内容为人们枯燥的疫情生活带来了色彩,也让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出前所未有的运动习惯。
2)居家健身符合当下时代需求
当前虽已处于后疫情时期,但由于新冠肺炎已成为全球传染性疾病,防疫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少出门、少接触”则是对自身健康安全负责的体现。秉持这一观念,大多数成员选择在家中进行体育活动,居家锻炼成为当下体育活动开展的最佳选择,也可谓是“最符合当代人需求”的体育运动方式。5G时代已经来临,网络越来越发达,关于家庭健身的课程愈加普及,例如当下十分火爆的Keep app,不论是私人定制健身计划,还是各类有氧无氧课程,都能在其中找到,可谓是居家锻炼的好帮手。居家健身,不仅节约了通勤时间,也打消了没有洗浴位置的担忧困扰,在享受到好的服务的同时,足不出户就可以取得去健身房一样的锻炼效果。
3.2 家庭体育面临的挑战
1)家庭体育环境缺失
家庭体育近两年逐渐兴起,由此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对家庭体育环境进行相关研究与探讨。陈智[18]认为家庭体育环境即家长和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之余以家庭为单位,影响家庭内或者家庭周边进行身体活动的因素(陈智)。他没有将家庭体育开展局限在家庭居室之中,而是将范围扩大到周边地区。阳佳鹏[19]认为家庭体育环境指影响家庭成员进行身体活动的各种家庭因素总和,其结构按文化结构三分法可以分为家庭体育物理环境、家庭体育行为环境和家庭体育心理环境。家庭体育物理环境是指家庭中促进或抑制青少年进行身体活动的器物,具体指家庭所拥有的体育器械和运动装备,家庭周围的体育设施(促进因素)以及家庭中所拥有的电脑、手机、游戏机等(抑制因素)。家庭体育行为环境是指父母与孩子进行身体活动的组织互动形式如父母与孩子共同参与体育活动、父母观看孩子参与体育活动、父母送孩子到体育培训中心学习体育技能或进行体育锻炼,父母鼓励、支持、督促或限制孩子进行身体锻炼。家庭体育心理环境指父母对孩子参与身体活动的期望信念和价值信念。武昌桥[20]则通过问卷分析得出家庭体育环境既要包括家庭成员特别是家长对体育活动的主观认识和态度、家庭及周边的体育氛围,也要包含开展家庭体育活动所需要的场地器材。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阳佳鹏学者对于家庭体育环境的概述相对全面和准确,他从物理、行为、心理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既包含了现实条件下的场地、器材、组织协调、行为等,也包含了理论上的知识方法认知观念等,因此,本文采用该学者家庭体育环境分析进行研究。
体育锻炼设备缺乏,社区资源配备不全面。体育锻炼的开展有时是需要一定的器械作为辅助支撑的。有研究表明,家庭体育设施充足可以使学生积极参与锻炼[21]。然而目前,在大部分家庭中,瑜伽垫是最常出现的锻炼设备,其次就是跳绳、杠铃片、哑铃等,很少会有跑步机、拉力器等专业的体育器械,大多专业器械体型庞大,占位且要花费不少的资金。放眼社区,社区中配备的都是只能进行强度较低的力量或有氧练习的设备,老年人使用较多,不太能满足年轻人要达到身体所需的运动强度。
有限的体育认知致使体育参与不积极,锻炼氛围不够。家庭体育的开展,除了硬件设施的要求,人们的意识行为对其也有很大的影响。张静[22]在关于父母体育行为对学生运动参与的研究中得出,父母体育认知程度有待提高;Adkins[23]等人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发现,父母的体育感知能力与支持情况和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况存在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只有认识的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才能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之中,进行体育参与行为。现有研究表明,父母在青少年体育中的作用已经从一开始的外在与旁观者变成支持与参与者。[24]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父母对子女培养锻炼习惯也起到促进作用[25](顾大成)作为家长,更应起到带头作用,先从自身开始,积极开展体育活动,以自身行为影响孩子,从而带动家庭体育开展,形成浓厚家庭体育氛围。
体育健康知识与技能缺乏。体育锻炼讲究合理性、系统性和有效性。要想通过体育锻炼达到想要的效果,就需要一定的知识与技能作支撑,在训练过程中不断调整并完善。学校体育以集体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体育锻炼能力,但针对个人体育锻炼内容较少,疫情下学生个人除了跟着视频学习以外自身缺乏相应储备,无法支撑更多体育技能的训练。有锻炼的想法,但却不知该如何实施,错误的锻炼方式也很容易使身体遭受损伤,进而终止锻炼行为。
2)“家庭”“社区”“学校”三者协同治理能力不足
学校体育是培养体育习惯的主体,家庭体育与社区体育则是对体育开展的基础和补充。当前,学校与社区体育资源开发尚不能对家庭体育形成有力支持,也没有较完善的政策与法律法规来指导它们资源调配。仅仅依赖学校与社区体育,它所带来的都是在某一范围内的锻炼效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青少年的健康促进难以奏效。在应试教育的深刻影响下,学校体育中学生主体性无法发挥,学生为了考而学,为了考而练,自主锻炼意识薄弱,体育技能与知识掌握情况较差;社区体育的开展则大多以老年人和幼儿为主,以健身器材为主要锻炼方式,体育活动途径单一,锻炼效果不佳;家庭体育目前也处于逐步发展时期,受众人群有限。因此,从学校到社区再到家庭的体育教育延续性被打断,无法持续作用使青少年产生养成良好的锻炼意识。
3)家庭体育锻炼模式单一
绝大多数的家庭在进行家庭体育锻炼时,都会采取大人陪同小孩或者大人自身进行锻炼的方式,很少会有所有家庭成员一起同时参与到体育锻炼之中,当幼儿在进行项目运动时,家人作为陪同者而非参与者,易让幼儿难以全身心投入到锻炼之中,持续性地进行锻炼。
4 家庭体育发展路径
4.1 体育锻炼设备的灵活运用
体育锻炼的方法多种多样,体育锻炼的器材也可以灵活变通。在家庭空间较小的场所,可以利用矿泉水瓶、沙袋一类的小物件代替杠铃等器材进行提拉、卧推等动作,通过改变水与沙的重量来调节自己适应的重量,利用毛巾、绳子一类的物品进行手臂、肩肘的训练,或者利用椅子、床头架等家具进行上肢或下肢的力量训练;在空间较大的场地,则可以将行进间的功能性训练作为主要的锻炼内容,垃圾桶、鞋子等都可作为功能性训练中的障碍来辅助我们训练。
4.2 “互联网+”背景下家庭体育资源开发
“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建立家庭体育线上平台,以家庭为单位入驻,平台上设置专业的家庭体育指导,让成员能有正确的锻炼方式与锻炼方法,同时,也有各种体育锻炼项目可以借鉴,或是以游戏的方式积分式的进行锻炼,让家庭成员在欢乐愉快的氛围中开展体育锻炼,既愉悦了身心,又健康了身体。
4.3 丰富家庭体育开展模式,营造家庭体育环境
家庭体育活动的开展,不应仅限于自主家庭体育活动。对于开展范围,可以延伸到各个家庭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社区与俱乐部之间,对于开展的形式,可以是开展各项体育赛事,或是举办体育文化交流节等活动。通过延伸家庭体育开展模式,增加各个家庭之间或是家庭与俱乐部间的交流,有助于相互吸取经验,与此同时,也能为不同类型的家庭提供多样化选择,以此吸纳更多的企业、组织等社会资源,开拓家庭体育发展空间,形成家庭体育发展新格局。
4.4 加强家庭体育宣传教育,推进社区、学校、家庭体育联合发展
加大家庭体育宣传力度,加强家长与孩子体育锻炼意识,提升家长及孩子对家庭体育认知,使其深入了解到家庭体育开展的积极影响,能投身于家庭体育的相关建设与活动的开展中。体育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时期或是某一个场所,终身体育理念才是全民健身时代所要追求的目标。因此,社区、学校、家庭三者不应作为互相独立的个体,也不能仅仅是单纯的合作,加强相互间沟通交流,形成合力,建立规范化模式,扩大体育锻炼范围,形成家、校、社一体化,促进相互资源协调利用,确保体育锻炼延续性。制定相应制度,更好指导学校、社区、家庭资源调配,不仅有利于各类家庭体育活动的开展,更能保障每个家庭享有平等开展家庭体育的条件,充分的发挥好家庭体育对社会体育的推动作用,也使得体育锻炼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于素梅.家庭体育锻炼:新时期学生健康发展不可缺失的一环[J].中国学校体育,2020,39(3):2-3.
[2]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2016-10-25].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3] 国务院办公厅.2019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EB/OL].[2019-09-0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02/content_5426485.htm.
[4] 王则珊,杨一庄.家庭保健体育实用手册[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0.
[5] 叶展红.关于开展家庭体育的构想[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1999(2):45-48.
[6] 刘江南,周在平,刘永东,等.穗、深、港家庭体育的比较研究[J].体育科学,1999(4):77-80.
[7] 张永保.家庭体育的内涵及其发展策略研究[J].四川体育科学,2020(4):88-91.
[8] 吴旭东.家庭体育教育是加强儿童青少年体育的重要基础和途径[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28(8):120-124.
[9] Jane E,RuseskiBrad R,Humphreys Kirstin,et al.Family structure,time constraints,and sport participation[J].European Review of Ag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2011,8(2).
[10] Anna.Direct and indirect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family physical activity environment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among 10~12 year-old European childre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and physical activity,2013(10):15.
[11] Åse Strandbu,Bakken A,Stefansen K.The continued importance of family sport culture for sport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teenage years[J].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2019(1):1-15.
[12] 徐恺.家庭体育观念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2019(9).
[13] 马德浩.从割裂走向融合——论我国学校、社区、家庭体育的协同治理[J].中国体育科技,2020(3):47-55.
[14] 栾文艳,张哲.近十年我国幼儿家庭体育研究综述——基于CNKI(2006年—2015年)期刊论文分析[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4):151-154.
[15] 陈智.体育中考背景下青少年家庭体育现状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1):62-66.
[16] 袁润,王红英,陈长洲.德国家庭体育的缘起、特征与启示.沈阳体育学院学报[J].2020(3):62-68+77.
[17] 国家体育总局.2018关于加快推进全民健身进家庭的指导意见[EB/OL].[2018-11-08].http://www.sport.org.cn/search/system/gfxwj/qzty/2018/1108/191882.html.
[18] 陈智.体育中考背景下青少年家庭体育现状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1):62-66.
[19] 阳家鹏,向春玉,徐佶.家庭体育环境影响青少年锻炼行为的模型及执行路径:整合理论视角[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3):118-123.
[20] 武昌桥.安徽省城市小学生家庭体育环境调查与分析[J].运动,2012(10):70-71.
[21] 阳家鹏.家庭体育环境、锻炼动机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关系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7.
[22] 张静.父母锻炼行为及其对小学生运动参与影响的研究[D].南京:南京体育学院.2017.
[23] Adkins,Sherwood Nestoiy.Mental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frican-American Girls:The Role of Parents and the Home Environment[J].Obesity research,2004,12(9):38-45.
[24] Ase Strandbu,Anders Bakken,Kari Stefansen.The continued importance of family sport culture for sport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teenage years[J].2020,25(8):931-945.
[25] 顾大成,华正春.广西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形成因素探讨[J].体育科技,2018(6):14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