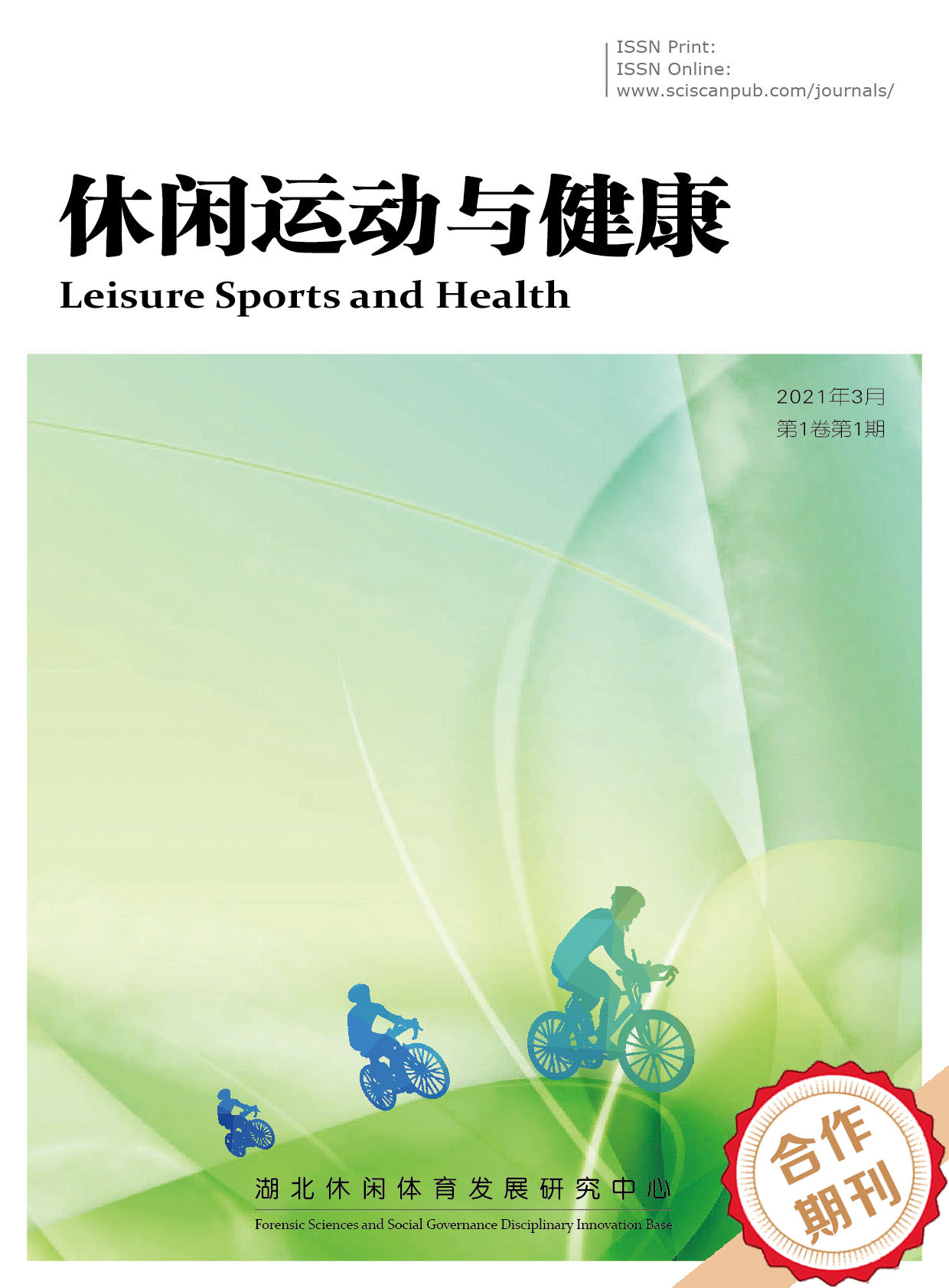Leisure Sports and Health
土家族“撒叶儿嗬”的体育发展基础与策略
The Sport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Strategy of Tujia “Saeerho”
- Authors: 杨玲¹²
-
Information:
1.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2.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62
-
Keywords:
Sayerho; Sports culture;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撒叶儿嗬; 体育文化; 民族传统文化
- Abstract: After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the tujia traditional sacrificial dance “Sayeerho” has been popular for a while, but in recent 10 year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ol. In the face of the success and confusion of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used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 field study and so on to study the sports development of “Saeerho”.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s of its sports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genetic significance,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ports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sports value, an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ports and art, expounds the advantages of sports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should meet the needs of leisure and fitness culture. Development goals should highlight the body training process; Development measures from “body” to “soul” for ceaseless and innovative. The specific aspects are as follows: first, content selection reduces the difficulty of artistic expression, so that sports are full of internal emotions; Second, the project selection breaks through the single project creation and editing, constituting the cultural adherence under the multiple choice; Third, on the level of promotion to exp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ports, build a solid social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two camps. 土家族传统祭祀舞蹈“撒叶儿嗬”经艺术转型后曾风靡一时,但近 10 来逐显清冷。面对艺术转型的成功与困惑,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对“撒叶儿嗬”的体育发展进行了研究。研究从发生学意义、艺术转型发展、蕴含的体育文化表现以及体育价值等方面阐释了其体育发展基础,通过体育与艺术的比较,阐述了体育发展优势,提出了策略。研究认为,在发展理念上要契合休闲健身文化需求;发展目标上要突出身体培养过程;发展措施上要从“体”到“魂”进行赓续与创新。具体如下:一是内容选编上降低艺术表达难度,让运动充满内在情感;二是项目选择上突破单一的项目创编,构成多元选择下的文化坚守;三是推广层面上扩大运动的参与人群,筑牢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两大阵营。
- DOI: (DOI application in progress)
- Cite: 杨玲.土家族“撒叶儿嗬”的体育发展基础与策略[J].休闲运动与健康,2021,1(1):82-89.
土家族“撒叶儿嗬”是一种古老的丧葬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撒叶儿嗬”研究与开发的文化艺人们,对原始的“撒叶儿嗬”进行了艺术加工改造,21世纪初以“巴山舞”系列舞蹈为新面孔的“撒叶儿嗬”曾风靡一时,甚至被誉为“东方迪斯高”。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当它处于顶峰时期,便是革新换面以求长足发展时期的到来,“巴山舞”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繁荣后,并没有迎来新的发展举措,以至于繁华过后逐渐清冷。笔者亲历了撒叶儿嗬世纪之交的发展,以学人的视野审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呈现的多学科特征,造就了研究领域的宽泛;而宽泛错综的涉足领域,又使研究多停滞于分析与赏析层面,似乎艺术转型的“巴山舞”就成为了无法逾越的至高。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需求而变化,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物质文化需求和美好生活向往在不断增长,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更加关注身心健康问题,希望通过自由自主的休闲方式健强体魄、缓解压力、抒发情怀。土家族“撒叶儿嗬”这种传统祭祀舞蹈,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带有精神情感的身体文化活动,充满传统的伦理情怀和人文关怀,对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规范行为等都有独特价值,不少体育项目的原型就出自这类文化活动。传统民俗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是传统文化面临的重要课题,把握事物的本质内涵特征,抓住突出的外在表象,多学科角度分析传承发展空间与可适性载体,是传统文化现代发展的根本。
1 土家族“撒叶儿嗬”的文化内涵与发展历程
1.1 土家族“撒叶儿嗬”的文化内涵
土家族以湘鄂渝黔边区的武陵地区为主要聚集地,“撒叶儿嗬”即“跳丧”或“跳丧鼓”是土家的一种祭祀歌舞。每有老人去世,停灵柩于堂前,亲属邻里前往吊唁。夜晚族民们“击鼓踏歌”,为亡人送行,通宵达旦,气氛热烈。它作为一种艺术化的风俗,不仅舞姿粗犷、曲牌丰富、唱腔古老,同时还是一种历史文化符号,承载着饱满的民族情节,蕴涵着深邃的哲学意义。
“撒叶儿嗬”的历史渊源有文献记载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而其源头可以从《巴渝舞》中找到踪迹,是土家先民巴人的军歌军舞;它的声腔歌调是一种古老的特性三声腔,歌种已成绝响,仅在跳丧时原汤原水地保存了下来;它尽管是祭悼亡灵的风俗舞蹈,但舞蹈表现的内容远远超出了祭祀范围,主要包括先民图腾、渔猎生活、农事生产、爱情及历史事件等民族发生发展的历史,表现了对民族历史的回忆和对祖先的崇拜[1]。“撒叶儿嗬”是土家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其豁达、通脱的生命观念非同等闲。
1.2 土家族“撒叶儿嗬”的传承历程
土家丧礼始于夏朝时期,最初形态是以祭祀白虎为主的系列歌舞。土家族“撒叶儿嗬”一直都处在传承与转型之中,第一次是在秦统一中原后的数百年间,其形式有过“绕尸而过”“以扣箭为节”到“打鼓踏歌”的演变,这些不同的形态和内容,就是不同流派的雏形;第二次是在清雍正年间,土家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后,土家文化与汉文化交融更频更深,原汁原味的土家“撒叶儿嗬”出现了许多变化,如生态环境、市场意识等;第三次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政治生态变化所致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出现了流变与转型,但“祖先崇拜”核心文化在土家地区并没消失,包括以战争场景模拟所表现的对先人尚武勇猛的歌颂,以及对战败迁离故土的缅怀;以情感和生殖膜拜表白的延续祖先血脉的执着狂放;以虎舞以及其他动物动作模拟、对生者赞歌孝歌等,宣示的对信仰乃至生命的崇拜等[2]。
土家族“撒叶儿嗬”集歌、舞、乐为一体,表演形式完美,表达了土家人的生死观和宇宙观,保留了渔猎时代和农耕文明的生活画面,积淀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遗存,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吸引了多学科领域的关注。2006年土家“撒叶儿嗬”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名录,传承人上至国家级、下至县级,各级政府给予工作条件支持。有一种传承是博物馆式保护与传承,是对原始文化的尊重,同时也能使若干年后还能见到原生态的真迹,为不同社会时期的文化转型提供原始素材;还有一种传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转型发展,创新出与现代社会相溶的新形态,让人类充分享受它给予的恩赐。就文化本身的价值而言,转型与发展是普识性认同,本世纪初吸取了“跳丧”元素的“巴山舞”便是转型与发展成功先例,是经过专家改编的“跳丧”准艺术转型[3]。
1.3 土家族“撒叶儿嗬”艺术转型的成功与困惑
20世纪70年代初,舞蹈工作者们开始对“撒叶儿嗬”进行创编,通过突出传统文化元素,以多种舞蹈套路出现在公众视野。改编之后的“撒叶儿嗬”以“巴山舞”系列舞蹈的形式存在,在内容的创编中,去祭祀化、去迷信化,改变了过去的丧味,选用与舞蹈情绪相符的民歌、山歌为基本曲调,并伴以弦乐,乐曲明快、鼓点清晰,整体效果上保留了原始狂欢性,步点跳荡、姿态优美、场面热烈。作为民族民间舞蹈,巴山舞经常在全国同类文艺展演中获奖,新世纪初曾以健身舞向全国推广,不仅受到了国人关注,甚至还被美国记者向全世界报道。
新世纪之交,鄂西地区掀起了巴山舞的学习高潮,发行了影音教材、成立了推广小组,组织了多期培训班,开展了各层面的表演比赛活动。经政府主导、媒介推动,巴山舞地域活化有声有色,踪迹遍布该地区企事业单位、中小学学校及社会民间组织;它还与旅游文化相结合,成为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亮丽的风景线[4]。但调查显示,近10年来巴山舞热度逐渐衰减,渐次退出群体活动范畴,它作为艺术的系列舞蹈对身体的姿态、动作的表现力、肢体的协调性、身体的意蕴性都有一定要求,离开了有组织、有规划的推广行动,靠人们自发参与,便会受到活动兴趣、身体基础条件等限制[5]。究其因,其一艺术转型的巴山舞对舞美有一定要求,它影响了民众的参与选择;其二巴山舞重“欢娱”、弱“豪壮”,民族“魂”的体现较为片面,文化根基不够扎实,这些势必造成离开外在强力行为,人群参与面便会断崖式下滑状况。文化的选择存在自主性,新时代背景下人们个性需求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现代成长”与“传统被发明”需结合新时代发展,从“体”到“魂”进行多学科多路径挖掘与创新。
2 土家族“撒叶儿嗬”的体育发展基础
2.1 传统与现代的“撒叶儿嗬”均含体育项目特征
土家族“撒叶儿嗬”作为传统的祭祀舞蹈,从表象上看更多的是情感表达,似乎与体育相隔甚远远,但从发生学意义上追溯,它与体育有诸多交融的地方。早期人类所有生活是浑然一体的,其生理、心理及社会文化都是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的,原始人的思维里万物是有灵的,他们相信生命、生育、狩猎、健康等都需神灵佑护,因而产生巫术魔法、图腾崇拜、宗教祭祀等活动,这些巫术、宗教、礼仪等仪式活动中,都离不开以身体运动为主要特征的舞蹈及身体艺术[6]。体育巫术起源论认为,不少体育项目的原型就出自于这些舞蹈与身体艺术,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体育的生发源头与发展动力。
现代转型中,脱胎于“撒叶儿嗬”的“巴山舞”亦是集合了身体运动、情感表达一体。关于体育,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体育概论》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将其定义为“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发展的文化活动”,认为体育的本质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7],舞蹈亦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发展的文化活动,显然这里舞蹈与体育没有明显的区分。也有研究从人的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理论出发,将体育定义为“以身体培养为基本特征的身体活动”,认为体育区别于其他身体活动的属性就是“以身体培养为基本特征”,并藉此辨识了舞蹈的学科属性,即“舞蹈的过程属于体育,舞蹈的效果属于艺术”[8],体育与舞蹈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原始的“撒叶儿嗬”,还是现代转型中的“巴山舞”,身体运动、身心发展是共同特征,本身就内含了体育项目特征。
2.2 土家族“撒叶儿嗬”蕴含了体育文化内容
物质与精神二元观认为,体育文化是有关体育现象中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即一定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长期从事体育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资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土家族“撒叶儿嗬”以身体活动为载体对生命意义的仪式化表达,与古希腊奥运会用身体活动祭祀酒神的狂欢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蕴含了体育文化意蕴[9]。结合传统文化固有的特点,以及体育文化的内涵外延,本研究从原本的技术、内隐的精神以及外显的审美等三个层面分析了“撒叶儿嗬”的体育文化内容。
1) 技术层面
运动技术是指完成体育动作的方法,是不同运动项目所富含的符合人体运动力学基本原理的标准技术。土家“撒叶儿嗬”集歌、舞、吹、打于一体,是一种综合的民间艺术,其本质上是一种民间祭祀活动,表现了土家人对先祖的崇拜。“撒叶儿嗬”步伐与姿态都十分讲究,核心舞段及基本动作是脚掌抓地、第一拍上步、第二三拍颤身,两腿交替进行,稳重有力;舞者一般保持一种弯腰、弓背、曲腿、臀部向下颤动的姿态。地域不同,步伐也存在一些差别,其中湖北巴东“撒叶儿嗬”中最具特色的是“四大步”,突出曲线美,音乐节奏为四分之三拍;湖北来凤、建始等县的“撒叶儿嗬”则多是“八字步”,显出稳重有力。参加舞蹈的多为二男、四男不等,高潮时百人、千人群体参加,十分壮观[10]。“撒叶儿嗬”动律固定、动作对称刚劲有力,有明显的运动技术要领和完成动作的方式方法,对身体也有独特的影响,显现了体育文化技术层面上的特征。
2) 精神层面
体育精神是指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品质、心理认知等。相关研究显示,“跳丧”源自古代巴人的军前舞,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颂扬生命鼓舞士气的战斗之舞衍生了土家“跳丧”的文化精神,土家“跳丧”最撼灵魂的是威武强劲的动律,以及狂放不羁的风格,这一显著特征自古存在,从未因时代更替、社会变迁而消失。也有研究认为,“跳丧”是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对生命的礼赞,“跳丧舞”就是生命重新开始的祝福仪式,寿终正寝者值得庆祝,歌舞中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积极人生态度[11]。就个体而言,他们认为老死是衰老的躯体重获新生的转折点,是“福”是“顺头路”,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转换;对族群而言,是减轻生存负担,为氏族的繁衍生存节省资源。这种超脱生死认识,对个体有解除痛苦与衰老的体贴,对群体有维护利益发展的关怀,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幸福平安渴望,以及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跳丧舞”表达和传承的豁达通脱生命观与群体文化观等精神层面的内容,以及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效益,与体育精神文化所表现的维度价值,如体育的理想、信念、节操,以及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等当属同一体系内容。
3) 审美层面
审美文化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美、享受美的一种特殊社会活动,是一种能够发挥精神教化的特殊形态方式,包括人类审美活动中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由此,运动审美文化不仅包括运动场景美、服饰美,也包括运动的形态美、意蕴美。“跳丧”跳的是一种阳刚美,远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期,其先祖巴人加盟于武王伐纣战斗,战前自由歌舞,记写了“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的辉煌篇章,不难想象巴人舞代刀的磅礴气势;“撒叶儿嗬”动作调度较有规律,“顺边下沉、晃悠、颤动”贯穿始终,展现了一种“反酮体”美,舞者身体在推进与拽拉、挺伸与缩进、展身与曲身、摇摆与抖动、振颤与晃动中展现出美来,这些都充分的展示了身体运动的健、力、美。同时,“撒叶儿嗬”存留着古代巴楚之地祭神乐歌的影子,且曲体结构与楚辞体式类似,展现了身体、音乐、情感交融的律动美、情意美[12]。
3 土家族“撒叶儿嗬”体育发展价值
相关研究对“撒叶儿嗬”的现代转型路径进行了剖析,就其原始功能弱化的现实,从适应新的社会生态环境出发,认为除了艺术外,更具优势的是体育。谢雪峰等将理由归为以下三点:一是土家乡民城市化变化,对现呈的“撒叶儿嗬”广场舞有新需求;二是人们寿命的延长使跳丧本身减少,体育扩展参与人群,能有效降低弱化;三是跳丧本身不乏体育成分,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体育活动。本研究在其基础上,从强健身心、扩大传承人群、运动文化育人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其体育发展价值[13]。
3.1 强健身心,运动效果好
“撒叶儿嗬”是歌、乐、舞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音乐、舞蹈与乐器是其精髓,其舞蹈特征总体上是弯腰弓背、翻掌穿肘、沉身颤动,因地域不同,舞蹈动作也稍有差异。 “撒叶儿嗬”姿态上是对各类动物的模仿,如“犀牛望月”“猛虎下山”“凤凰展翅”“猴子爬岩”“燕儿含泥”“狗连档”“美女晒羞”“乡姑筛箩”等,其中最为壮观的是“猛虎下山”,舞者跳着跳着,忽然鼓点一变,对舞的人突然跃到空中,掀挑舞伴,两人躬身逼近,撞肘击掌,前跳后扑,上下呼应,类似猛虎扑食,最后一“虎”被挽,伴以啸啸虎鸣从头顶后空翻跃过,动作威猛逼真。
这种以身体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不论其文化内涵有多么深刻,呈现的首要特征是身体运动,从头到脚、从躯干到四肢,动作幅度大,跨步与跳跃转换频繁,全身抖动结合,表现出高运动强度特征。原始的“撒叶儿嗬”有固定套路,在特有的活动场景中伴着激越的节律,成年男子跳上一阵子便大汗淋淋,需场间换人,它高运动强度特征有极好的健身效果,伴以的音乐场景还能抒发情怀,身心都得到了锻炼。
3.2 参与人群广,影响范围大
“撒叶儿嗬”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性的自由随性活动,没有师承关系、不用拜师学艺,想学的人就在白喜事现场跟着老艺人学习即可。有报道写道:丧鼓分秒必争响起,参加跳丧的人不分长幼年龄与身份贵贱,只要来参加丧葬仪式的男性均可到队伍中来,主跳的人在中间,围观的人伺机入队。气氛浓厚时,站前面人群跃跃欲试,后面的踮着脚往前挤,鼓声中歇,立刻有人被拥进去,原先队中的人也有被挤出的,只好无奈下场,等待再次机会。歌师与鼓师场上活动也比较随意,他们可以边唱边歇,还可以自由出入,也可随时加入跳丧人群,整个场面热闹、氛围宽松[14]。
现代化进程中,改编后的“撒叶儿嗬”不仅走向了民族艺术表演舞台,而且还变身广场舞,从灵堂走向了广场、从乡村走向了城市,原生态在时代变革中派生出分支,民俗得到了衍生。20世纪90年以后,县级及以上城市均建设了文化广场,广场舞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转型之后的巴山舞经培训推广,风靡了民族地区,引起国人关注。尽管当前离开外力推动呈低迷状态,但它的集体性形式表明了该活动的受众面。从体育的角度进行挖掘创新,体育与艺术等多学科发展相辉映,参与人群与影响范围能进一步拓展,传统民俗文化在全面滋养现代生活的同时,自身也得以了更广泛的传承与发展。
3.3 能弥补原始功能的不足
原始“跳丧”有诸多社会功能,如生命观的形成、民族精神的塑造、民族凝聚力体现以及娱乐休闲作用等,它所呈现的生命观是“死亡是人生命中所必须经历的历程,如春夏秋冬季节变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15];而“人死众家丧,一打丧鼓二帮忙”“人生不计死仇,亡者为大”又体现了原始群体意识与团结互助习俗;“撒叶儿嗬”歌词中有“先民在上,尔土在下,向王开疆辟土,我民守土耕稼”等句子,无不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
以体育为发展与传承路径,原始的生命情怀、民族精神未变,不仅能体现以上功能,还能弥补“跳丧”功能的不足。体育本身就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体育文化既体现在运动技术掌握、体质健康增强等表象的静态文化层面,又体现在体育精神培养、体育人文美体验等深层的动态文化层面[16]。体育人文美中的对运动项目的审美体验,机体刺激的身体体验,以及参与运动的情感体验,都能较为清晰地凸显运动的价值功能。从体育文化角度出发进行“跳丧”传播与传承,除了能实现原本祭祀活动的教化功能外,还具有健身功能、人际交往功能、休闲功能等运动文化功能。
4 土家族“撒叶儿嗬”体育发展策略
4.1 发展理念上契合当代休闲健身文化需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倾向选择放松自我、缓解精神疲劳与压力的休闲健身文化活动,所谓休闲即包涵了自主自愿、兴趣兴致等关键要素。人类学家认为,体育既是规则下的竞技活动,也是集工作、休闲、玩耍为一体的具有仪式性和游戏特征的社会实践模式。体育的多功能性特征弥补了“撒叶儿嗬”艺术转型的不足。艺术转型的巴山舞以系列舞蹈形式存在,共由8套舞蹈和乐曲组成,分集体舞、双人舞、单人舞等多种。巴山舞动作舒展、节奏明快,充分展示了身体的姿态美与律动美,新世纪初占领了该地区文艺活动阵地,从舞台到大众健身文化生活随处可见,但现今群众自发参与人数骤减,基本又回到舞台表演形式。调查显示,目前尚还参加广场巴山舞锻炼者都有一定的文艺基础,不少还是文化战线退休职工,很多民众想加入又难以掌握动作技术。显然过去高参与度与专门培训实施是分不开的,离开了职能部门的普及,巴山舞便失去了成长的空间。
自主自由的运动参与、兴趣娱乐的活动过程、非功利的活动心态、身心统一的活动效果等是休闲健身文化活动的特征[17],传统民俗文化有自身的思想体系,身体活动受感性支配,“体”的表现自由随性,“魂”的表达内涵丰富,它与现代休闲文化生活需求高度切合[18]。立足传统文化的“现代成长”与“传统被发明”,以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为基准[19],从“体”到“魂”挖掘与体育联系紧密的形态内容,打造与社会发展及人的需求相适应的自由、自主的健身文化内容,应是土家族“撒叶儿嗬”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
4.2 发展目标上突出体育身体培养过程
从体育角度探寻传统文化的发展,不仅要明晰它与本学科的关联,还需明晰它与相邻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以便于对比优势,扬学科之长。体育角度研究“撒叶儿嗬”主要藉于其“身体运动”特征,而该特征也同样适宜于舞蹈,转型的“撒叶儿嗬”(巴山舞)就是以系列舞蹈呈现的。舞蹈与体育的关系迄今理论界没有科学的解释,体育界认为舞蹈属于体育,艺术界认为舞蹈属于艺术。体育与艺术在表现形式和效果上虽有渗透的成份,但毕竟属不同的学科门类,都应有学科的独特性。相关研究认为,从本质特征出发体育主要强调的是身体培养的过程,注重身体的教育训练,而艺术则强调表现的效果,讲求生活、思想和情感的肢体化表达。诚然体育难美类或操化类项目中也会存在思想情感等艺术成份,被称为“艺术化的体育”,它是在身体培养过程中产生了艺术化效果,与艺术学的舞蹈目标是不同。
在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的今天,参与广场舞健身的人群已全面扩大,有学生族、上班族、退休族等,年龄性别不限,已突破了过去“广场舞大妈”的面貌。如此庞大的人群在项目内容选择上理应有区别,但本研究团队在多城市及乡村调研发现,人群聚集最多、最有气场的是音乐节奏明快、步伐特色明显、上肢动作简单的操化锻炼内容。这些操舞内容动作固定、循环往复,更多突出的是身体锻炼的过程,而不是身体的艺术化表达,调查表明突出身体培养的艺术化体育比突出效果的艺术化舞蹈更受普通人群的喜爱。把握体育本身所持有的不同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以突出身体培养过程为根本,在解决人们所需的实质性问题上发挥独特价值,是土家族“撒叶儿嗬”的体育发展目标。
4.3 发展措施上体现从“体”到“魂”的赓续与创新
1) 内容选编:降低艺术表达难度,让运动充满内在情感
以体育为路径创新发展“撒叶儿嗬”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身体,它与艺术路径发展的效果是有区别的。文艺工作者们在创编巴山舞乐舞套路时尽管选取了传统“撒叶儿嗬”的步伐及耸肩下颤等身体动作特征,但更倾向于以优美的姿态表达情感,8套舞蹈分别有“喜鹊登枝”“百凤朝阳”“风摆柳”“巴山摇”等舞蹈词汇及情景主题,对练习者身体协调性、音乐感知力肢体表达力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这些身体素质条件不具备,练习者的愉悦感、健身性及自我实现等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备受打击。
以培养身体为目标的体育创新发展就是要针对这些现实问题,从身体动作的组合、音乐节奏的把握、情感表达的形式等进行赓续与创新,突破现行乐舞套路“体”的动作套路细碎复杂,“魂”的肢体表达艺术化成份高等局限,改善它在大众需求方面的不足[20]。具体内容选编上可作如下定位:其一,突出“撒叶儿嗬”典型动作特征,如下肢的四大步步伐、上体的手足同边,以及身体规律的颤动、双肩上下扭挫等,减少上肢的舞蹈动作设计并降低舞姿要求;其二,多身体培养内容,注重运动的科学化,讲究肢体运动的顺序,运动负荷的大小;其三,变换情感表达形式,改善巴山舞以身体姿态呈现情感表达方式,让运动充满内在情感,即在具身体验中以情绪情感的交融体现“撒叶儿嗬”的“魂”——祈愿。
2) 项目选择:突破单一创编形式,构成多元选择下的文化坚守
“撒叶儿嗬”的传承一直以来都是以舞蹈的形式呈现,无论它是艺术的舞蹈还是艺术化的体育,均体现了较好的健身健心功能,它所呈现的集体操舞形式、优美的曲风、亘远的民族情怀,是人们喜爱的重要因素。分析“撒叶儿嗬”的本质内涵,身体活动是载体,情感表达是主线,如果离开情感氛围,身体活动可被任何其它项目替代。由此,立足民族项目中情感内容的要素,全面体现内在“魂”才是民俗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关键。艺术转型的巴山舞更多体现的是劳动欢娱、丰收喜悦、生活祥和等生产生活,它仅是 “撒叶儿嗬”集体情怀的一个方面。回溯 “撒叶儿嗬”的民族情怀,有对先人尚武勇猛的歌颂,对战败迁离故土的缅怀,以及对生命赞歌礼颂等,这些都以模拟虎舞以及其它动物动作呈现,巴山舞的创编中“欢娱”得到了很好的延伸,而“豪壮”显现不足,民族“魂”的体现不够全面。
以体育为发展路径,能通过拓展项目的类型来拓宽民族“魂”的表达。一方面对巴山舞系列舞蹈进行创新完善,内在情感与外在欢娱结合,深层次的显现“撒叶儿嗬”本身所表现的祈愿;其二进行操化类套路设计,选取其基本律动元素,如动作的顺边反跨、身体的下沉颤动等,改编成步伐套路固定、简单易学又有较强健身功能的操化套路;其三突出“仿生性”特征,进行项目拓展,如武术,“撒叶儿嗬”本身模拟的就是动物活动,它突出一个“虎”字,即模仿老虎相互进退、撞击、跳跃、旋转等。舞者在腾空中展现出英姿飒爽的“虎威”,进腿躬身,腾空扑地,错落有致,一跃一跳,活灵活现,这种表现在武术中早有对应的项目“五禽戏”,借助“五禽戏”的思路进行体育项目融合创编。无论是何类项目身体活动只是外在的肢体表现形式,真正维系民俗文化传接与发展的还是内在民族“魂”的表达,这就需要创新发掘中“感情准则”的坚守,通过文化环境、民俗元素等达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实现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的多重功效。
3) 推广领域:筑牢“学校”“社会”两大阵营,扩大运动的参与人群
社会体育领域是推广的基础阵地。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各地政府常常通过组织传统文化活动进行宣传与繁荣地方经济,这种活动表演只是表层的推广,效果影响只是一时的,未能真正扎根[21]。社会体育领域包涵群众体育与大众体育两个层面,涉及的人群广阔,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以及乡村农民等,在人民生活水平生命质量逐步提高的今天,体育锻炼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无论是以健身、健心、健美为宗旨,还是以娱乐、医疗、交友为目的,进行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身体锻炼活动已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体育为发展路径进行“撒叶儿嗬”创新发展,外观上保留原始动作特点、独特的巴楚音韵,内涵上表达深刻的民族情怀,凸显民族文化所富含的精神,通过身体动作与情感体验的交融,感受运动文化的深层魅力。
学校体育教育是传承的核心阵地。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融入,加强地域文化根基的构筑,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有效路径。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纲要明确指出,结合校本传统与优势,进行校本课程研发。近十年来,鄂西恩施地区及湖北长阳、五峰等县区中小学将巴山舞作为课间操进行锻炼,增强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有力的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但调查显示,部分学生认为过于舞蹈化,不太适合课间操锻炼;也有同学认为时尚风格缺乏,与学生的需求与兴趣不切合,尤其是男同学大多不喜欢巴山舞,认为太“娘们”,而原始的“撒叶儿嗬”只有男性才能参与,且舞步粗犷,这又一次显现了艺术转型的巴山舞存在的不足。文化生态观点认为,地域文化情感的培植,是传承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在现代文化日益丰富的今天,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融入,要从民族文化认同出发,注重文化情感的培养,这样才能使学习兴趣更为持久、技术沉淀更为长久。
5 结语
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体现,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任重道远,纵观“撒叶儿嗬”原始文化特点及转型发展经历,除了艺术外更具优势的是体育。无论是传统的“撒叶儿嗬”祭祀舞蹈,还是艺术转型的“巴山舞”系列舞蹈,它们都是以身体活动为载体展开的,均含体育项目成份与体育文化表现。传统的“撒叶儿嗬”祭祀舞蹈粗犷豪放、动作幅度大、步伐稳健,体现了高运动强度特征,但它是一种丧葬文化,必须在特定的环境才能进行,而且性别、年龄都受到了限制;艺术转型的“巴山舞”吸取了“撒叶儿嗬”之精华,在音乐、舞美、情感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发展,去除了丧味,突破了人群环境限制,曲调清新悠扬、舞姿优美舒展、情感激越跳脱,但它相对于普通人群艺术成份高,且在民族魂表达方面较为片面。随着社会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内容与形式都在发生变化,自主自由的感性健身文化更切合人们的需求。
以体育为发展路径要立足本学科功能属性,挖掘原始文化与之相关的形态内容,借鉴“巴山舞”艺术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从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措施等方面进行统筹布局。在发展理念上,需剖析新时代背景下大众健身文化特征,保持传统动作特征、音韵风格,打造与社会发展及人的需求相适应的自由、自主的健身文化内容。在发展目标上,辨识体育与相邻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以突出身体培养过程为根本,在解决人们所需的实质性问题上体现独特价值。在发展措施方面,从“体”到“魂”进行赓续与创新,在内容选编、项目选择、推广领域上下功夫:一是突破现行巴山舞乐舞套路高艺术局限,精选典型动作,注重运动的科学化,降低肢体艺术化表达难度,在具身体验中以情感交融体现“艺术化的体育”;其二通过挖掘原始“撒叶儿嗬”的“仿生性”特征,借助“五禽戏”的思路进行项目融合创编,突出虎威,改善现行乐舞重“欢娱”、轻“豪壮”的不足,全面体现“撒叶儿嗬”内在“魂”,构成多元选择下的文化坚守;其三筑牢“学校”“社会”两大推广阵营,学校体育层面做好民俗体育课程开发与实践工作,社会体育层面进行休闲健身文化创新活动,以不同于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吸引更多的民族参与,成为人们在闲暇的、自由支配的时间里进行身心锻炼的行为选择。
参考文献
[1] 田万振.土家族生死观绝唱——撒尔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 黄柏权.土家族白虎文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3] 徐瑞琳.关于长阳土家族巴山舞传承与发展的研究[J].北方音乐,2019,39(17):228-230.
[4] 汤立许.传统体育地域活化的路径研究——以长阳巴山舞为例[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4(3):40-44.
[5] 马依鸣.长阳地区土家族“巴山舞”传播发展现状研究[J].传媒论坛,2019,2(14):165-166.
[6] 杨日.历史·文化·身体——土家族跳丧记忆的承传与重构[J].大众文艺,2015(2):63.
[7] 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2-36.
[8] 梁红梅,李金龙,李梦桐.体育概念的重新界定[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1):100-103.
[9] 覃兴耀.土家族跳丧舞的体育文化学意义[J].湖北体育科技,2015,34(11):975-978.
[10] 白晓萍.撒叶儿嗬:清江土家跳丧[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
[11] 张伯瑜.生死都是一首歌——观土家族跳丧“撒叶儿嗬”有感[J].人民音乐,2017(5):42-45.
[12] 杨光.土家族“跳丧”文化中的舞蹈探索[J].课程教育研究,2018(21):226.
[13] 谢雪峰,刘俊梅,李芳,等.土家族”跳丧”文化传承与转型若干问题的探讨[J].体育科学2011(7):17-22.
[14] 向远虎.论“撒叶儿嗬”中的原始生命意识和狂欢化特色[J].文学界:理论版,2012(2):54-55.
[15] 白晓萍,撒叶儿嗬:清江土家跳丧[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
[16] 柴娇.体育课程的运动项目文化教育回归与困境破解[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6):81-97.
[17] 杨玲,韩双双.“滁人游”的休闲体育文化表现及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2016(4):161-164+182.
[18] 祖庆芳,邢文涛.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的体育娱乐精神[J].浙江体育科学,2016(3):44-49.
[19] 罗湘林,郭汝.传统民俗的体育化路径探析——基于巴山舞的审视[J].体育科学研究,2019,23(4):1-5.
[20] 李芳,史晓惠,谢雪峰.土家民间舞在健身舞蹈中的运用与开发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5):86-90.
[21] 倪依克.蒸腾与困窘:当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之惑[J].体育科学,2005,25(9):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