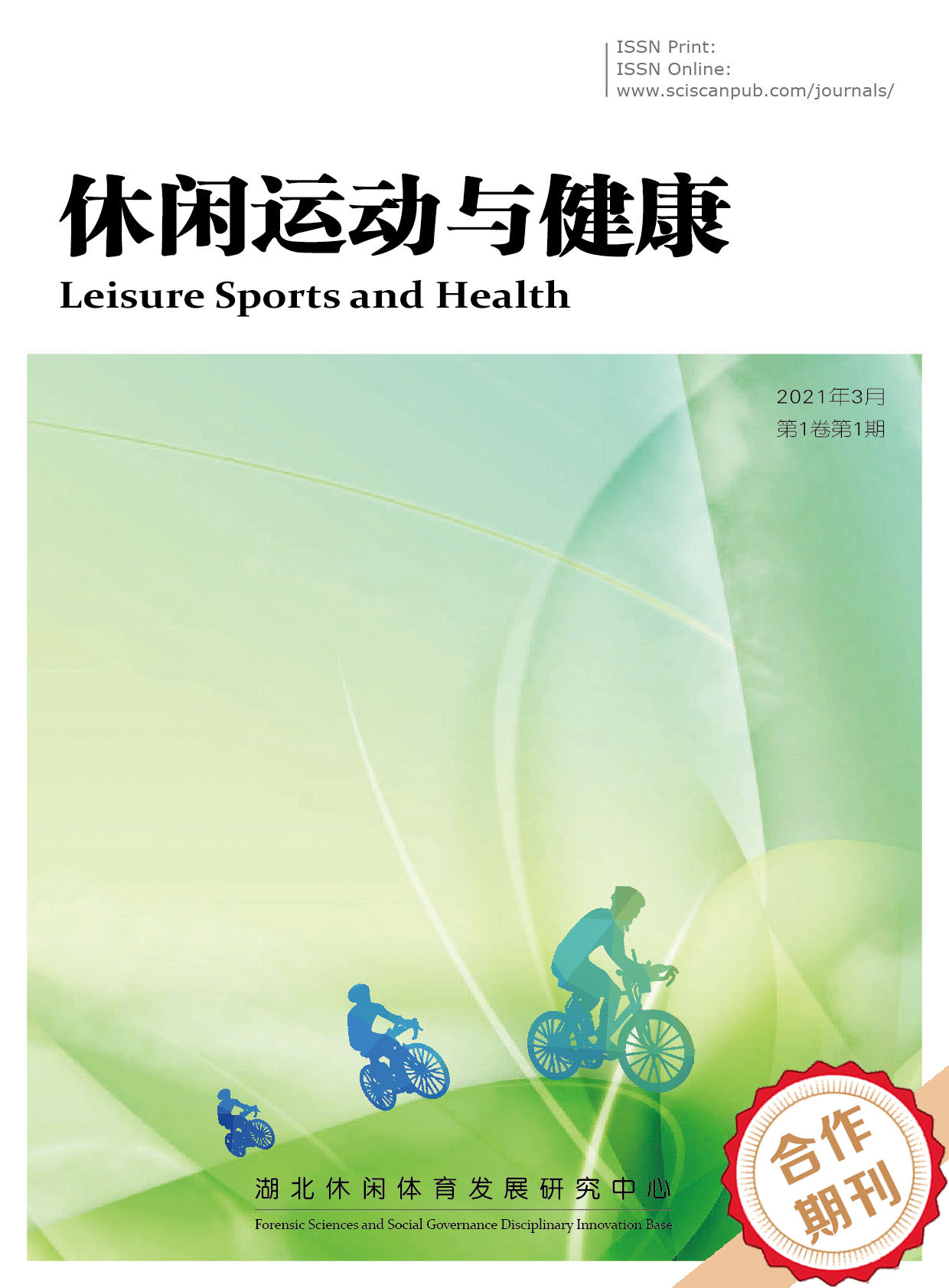Leisure Sports and Health
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对照护机构老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
Effects of Animal-assisted Leisure Activity to Rest Home Elder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 Authors: 潘丽雯¹ 叶怡矜²
-
Information:
1.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2.台湾体育大学休闲产业经营学系,台湾桃园 333325
-
Keywords:
Aging; Animal-assisted leisure activity; Rest home; Recreation therapy高龄化; 休闲治疗; 动物辅助休闲活动; 照护机构
- Abstract: Purpose: Aging society becomes a globing phenomenon. The busy society lifestyle, different marriage forms, low birth rate, and life span extension are making the issues of aging society more severed. However, lacking companions and siblings aggregate elders’ social support issues.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studies in U.S.A. and Europe, playing with pets and animals provides the source of comforting and sense of companionship. In the different cul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leisure therapy’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effects by applying animal-assisted leisure activity (AALA) to rest home elders. Method: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were elders who resided in a private rest home in northern Taiwan.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a one-hour a time and 6 times a week longitudinal AALA experiment to the experimental (AALA participants) and control group (AALA non-participants) elders for 6 weeks.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 and on-site observation were applied for both groups. Results: In the physical health aspect, the AALA had slightly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two groups’ elders. Additionally, in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health aspect, the experiment group had improved much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elderly who lived in the rest home for a long time were obviously unabl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By applying AALA recreation therapy, the elders’ physical,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ense of social support had been improved, especially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ense of social support. 目的:全球高龄化现象日趋显着,再加上工商业社会繁忙、婚姻结构改变、少子化及人类寿命延长的现象,使高龄化的问题更为严峻,而缺乏亲友子女长期陪伴加重了老人社会支持问题。在欧美相关的研究中指出,动物在人情绪低落时具有抚慰的力量与促进身心健康的效益,因此在不同文化下,本研究目的为应用动物辅助休闲活动,探讨休闲治疗对照护机构老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方法:本研究对象为台湾北部某私人照护机构之老人,研究设计为期六周共计六次之纵断性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实验研究,研究方法将老人分成实验组(参与活动)与对照组(未参与活动)各 6 位,研究工具与资料收集采用动物辅助休闲活动量表、访谈法以及现场观察方式,再进行活动前后两组数据的比较。结果:在生理健康方面,参与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对老人生理健康稍有正面改善;在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方面,参与动物辅助休闲活动之老人其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之改善明显高于未参与活动之老人。结论:长期居住照护机构之老人,其生活明显无法自理,但导入以休闲治疗为目的之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后,其身心健康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DOI: (DOI application in progress)
- Cite: 潘丽雯,叶怡矜.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对照护机构老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J].休闲运动与健康,2021,1(1):57-63.
全球高龄化现象日趋严重,中国也无法置身事外。根据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已达8,830万人,占总人口的7%①,而台湾截至2020年3月底统计,老年人口总数约366万人,占总人口数更高达15.5%②,依据联合国“高龄化社会”标准,均早已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门坎,这样的数据也显示出相关老龄生活之研究已刻不容缓。
反思现今有关生活在照护机构之老人研究大都偏重在照护、医疗与健康相关领域,甚少触及居住、经济、社会适应以及休闲等方面,因此本研究从生活概念思考高龄需求,结合休闲活动探讨照护机构老人之身心健康与社会健康的关系。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质性研究之实验法为研究主轴,辅以量表施测,研究对象为居住于台湾北部某私人照护机构年满65岁及以上之非完全独立生活且其日常生活仍需要不同程度协助的老人。入选标准:①属长期居住者,且居住满一个月以上;②意识清楚、无精神障碍,可以口头回答或自行填写量表;③无语言障碍能与人沟通者;④经说明研究目的,愿意参与研究;⑤需经家属同意并签署研究对象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①人口统计变项,包括性别、生日、婚姻状况、子女数、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经济来源、退休前职业。②生理健康量表(巴氏量表),内容包括进食、移位、个人修容及卫生、沐浴、如厕、行走、上下楼梯以大小便控制等10个项目,其特色为具有操作型定义及评分标准化之优点,评分方式依据受试者之独立或需协助之不同,各有不同之加权计分,最低0分,最高15分,总分100分,0~20分表完全依赖、20~60分表严重依赖、61~90分表中度依赖、91~99分表轻度依赖及100分完全独立五个区间,再测信度为0.89,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检验结果显示巴氏量表具有极高之稳定性。③心理健康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正负向情感出现频率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采Likert五点量表计分,由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总分介于5至35分之间。正、负向情感频率之测量(PA/ NA)共计8题,分别以八个情感性字汇代表,正向情感为“爱、喜欢”“高兴、喜悦”“满足”“自信、自豪”;负向情感包括“害怕、恐惧”“生气、愤怒”“悲伤、难过”及“自责、内疚”。受试者依过去一个月内所感受这些情感之发生频率选取适合选项并计算得分,分为“从未经历”1分到“总是经历”5分,总分为40分,依据得分高低,评估其正、负向情感出现之频率,用以了解老人情绪之反应。④社会健康量表(社会支持量表),采用张素红于1996年根据Barrera 等(1981)所编的社会支持行为量表(Inventory of Socially Supportive Behavior,ISSB)所修订之量表,共计13题。量表内容涵盖社会支持行为与社会支持来源,采Likert 3点计分(1分为“从不”;2分为“偶尔”;3分为“经常”),总分为13~39分,分数愈高代表社会支持度愈高[1]。⑤访谈大纲分五大类12小题与一题开放式题目。
1.3 研究方法
1) 实验限制
完成研究工具预试与修正后,确定研究人数,立即进行老人日常生活纪录检视,筛选适合之老人进行分组调查。本研究因研究对象患有慢性病患或日常生活不同程度无法自理,故无法随机指派研究对象到实验组或控制组,故其研究属性为有别于“真实验设计”之“准实验设计”[2]。
除此类似相关研究操作,在台湾尚属先驱性研究,故以社区化小型照护机构为本研究场所之首选。另考虑动物特性及研究对象之特质与安全,犬类动物与人类一起生活时间久远,且为一般家庭常见之宠物,因此选择犬类作为本研究之中介变项。再则考虑到实验设计,以能主动亲近老人且为健康、无安全疑虑之犬类为最佳。由于黄金猎犬喜欢被宠爱、会主动与人亲近的特性、温驯及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强,适合被动的老人,故选定黄金猎犬为辅助本研究之动物。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以动物辅助休闲活动(AALA)为中介变项,经检视老人日常生活纪录与老人意愿后,最后筛选出12位老人加入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参与AALA之老人)与对照组(不参与AALA且维持原来日常活动之老人)各6位。实验期间6周,每周1次,每次活动1个小时,连续6周6次活动,不同组别之研究对象均须完成活动前测、后测与访谈。
1.4 资料分析
(1)撰写访谈逐字稿:即研究者与访谈者的对话内容,目的是希望能够更清楚的纪录访谈过程。
(2)以动物辅助休闲活动、身心健康为基础架构,以闲聊方式进行后,再由研究者自访谈内容中抽取该段话语的关键意义,进行重点句的摘录,重新组织使其较具逻辑性。
(3)根据访谈大纲的主题归纳、分类数据呈现之结果,并与量表结果进行比较、讨论。
(4)以方法三角测量法为资料分析依据,将访谈资料整理、分析并与量表结果、研究者观察记录进行统整,以期能得到客观中立之结果。
2 研究结果
2.1 生理健康状况分析
(1)自觉健康状况改善实验组较对照组明显。实验组有2位自觉健康有改善,2位持平,2位觉得健康较差。对照则5位持平,1位降低,表现无明显差异。
(2)功能健康状况表现无明显变化。不论实验组或对照组,生命征象或巴氏量表变化在前、后测之结果差异不大。在巴氏量表部分,实验组即使得分改变,但在得分间距上,仍属同一级数,无法视为显着改善。
2.2 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1)生活满意度得分实验组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前测总分86分,平均14.3分,后测总分108分,平均18分;对照组前测总分76分,平均12.7分,后测总分77分,平均12.8分。
(2)正、负向情感出现之频率改善实验组优于对照组。实验组正向情感前测总分74分,平均12.3分,后测总分100分,平均16.7分;负向情感前测总分49分,平均8.2分,后测总分33分,平均5.5分。对照组正向情感前测总分66分,平均11分,后测总分63分,平均10.5分;负向情感前测总分59分,平均9.8分,后测总分60分,平均10分。
2.3 社会健康状况分析
(1)社会支持行为总得分实验组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前测得分介于149~201分之间,对照组前测得分介于132~204分之间。后测时实验组得分已扩大,介于132~212分之间,对照组得分则明显降低,介于113~186分之间。比对活动前后2组数据,对照组在整体比较上,其所获得社会支持行为已明显少于实验组,见表1。
表1 社会支持行为总分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s in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behavior
| 组别 | 情绪支持 | 社会整合 | 信息支持 | 实质支持 | 尊重 | |||||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
| 实验组 | 190 | 202 | 201 | 212 | 121 | 132 | 189 | 198 | 149 | 144 |
| 对照组 | 191 | 177 | 204 | 186 | 132 | 113 | 193 | 173 | 144 | 116 |
(2)社会支持来源以子女及医护人员为主。不论实验组或对照组,在前测或后测表现都是以来自子女及医护人员的社会支持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社会来源。另在配偶部份,由于大部分丧偶或因个人已入住照护机构,故配偶得分较低,无法成为主要社会支持来源,见表2。
表2 社会支持来源总分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in total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 sources
| 组别 | 配偶 | 子女 | 亲戚 | 邻居 | 朋友 | 医护人员 | 传播媒体 | |||||||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前测 | 后测 | |
| 实验 | 81 | 82 | 170 | 192 | 114 | 109 | 96 | 79 | 100 | 133 | 157 | 172 | 132 | 121 |
| 对照 | 104 | 104 | 177 | 173 | 103 | 86 | 102 | 81 | 103 | 87 | 153 | 128 | 122 | 106 |
(3)社会支持满意度总得分实验组高于对照组。在实验组方面,前测总分为234分,平均得分为39分,得分区间介于28~50分之间,有3位高于平均值,1位平平均值及2位低于平均值;后测时总分为239分,平均得分为39.8分,得分区间介于34~46分之间,有2位高于平均值,4位低于平均值。在对照组方面,前测时总分为227分,平均得分为37.8分,得分区间介于33~41分之间,有4位高于平均值,2位低于平均值;后测时总分为221分,平均得分为36.8分,得分区间介于31~41分之间,有4位高于平均值,2位低于平均值,见表3。
表3 社会支持满意度差异
Table 3 Differences in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satisfaction
| 实验组 | 对照组 | |||||||||||||
| 编号 | E1 | E2 | E3 | E4 | E5 | E6 | 总分 | C1 | C2 | C3 | C4 | C5 | C6 | 总分 |
| 前测 | 50 | 41 | 40 | 39 | 36 | 28 | 234 | 33 | 39 | 39 | 39 | 36 | 41 | 227 |
| 后测 | 46 | 39 | 43 | 39 | 38 | 34 | 239 | 31 | 38 | 35 | 39 | 37 | 41 | 221 |
| 差异 | -4 | -2 | 3 | 0 | 2 | 6 | 5 | -2 | -1 | -4 | 0 | 1 | 0 | -6 |
2.4 访谈资料归纳与分析
1) 外在环境影响生活状态的认知
不论实验组或对照组,老人对整体生活环境的认知、服务质量、环境设施、硬设备、物质要求、餐饮及休闲活动规划上要求不多。对生活状态之满意程度,其回答也以“满意”居多。但生活在照护机构老人的身心状况所展现出来对生活状况的看法,有着耐人寻味的地方。其一为满足的标准降低,其二为对本身状况的无奈。在这两种心理状态的交错运作下,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满意”,而这种“满意”的现实意义实大于理想意义。对照护机构的老人而言,“满意”是相对于目前个人身体状况的产物,而不是达成理想生活的结果。因此,“有吃有住”就能满意了,甚或表示“活到现在很多事应该要满意了”。除此以外,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行动能力,尤其行动能力深深的影响着老人对于日常生活之满意程度。因其行动不便所衍伸出来的“让人操烦”(操心烦恼之意)的负面情绪以及生活圈的缩小,都让照护机构老人对生活满意的想法中隐含着颇难捉摸的情绪。
在高龄期这个阶段,对老人而言,目前生活状况之满意程度,似乎不那么重要。由于老人已历经人生各种阶段,故在说法上会以较含蓄的方式表达或不敢说出内心真正想法,因此较易产生合理化的社会性回答,故而很难真正了解其对生活状态之真正想法,但由此具有特殊意涵的“满意”回答与否与社会健康之满意程度比较,正可说明何以满意程度总得分不论实验组或对照大部分很高,但相较量表测量结果,却发现不符,可以解释为何社会健康“满意度”构面与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程度很低的原因。
2) 对外在安慰协助与支持的认知因素探讨分析
在本研究12位研究对象中,社会支持来源以子女得分最高,其中一位因经济因素,照护费用由子女和其弟妹各负担一半,所以其社会支持来源,亲戚支持得分高于子女,但大部分子女仍是照护机构老人精神上的主要支持。丧偶(8位)或没有住在家中则为配偶非成为主要支持来源的原因,然而由于非住在家中,所以亲人无法经常到照护机构探视老人,因而需借助其他力量以慰藉其精神,例如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带给照护机构老人的最大影响层面以内在心里为主。老人普遍表示宗教能带给他们“心灵较平静”“会对他人较好”“不要让自己想太多”“对事情比较不会执着”。因此宗教信仰对老人而言,不仅能改善心情,更能维持心灵上的平衡,具有倾诉、转移老人心里空虚及转化心里层面不满的功能,对老人之间的人际互动有着正面的意义。
另外,生活在照护机构除了明确代表需要照护或生活无法自理之外,其中一个背后涵义就是需要陪伴。需要陪伴让医护人员成为社会支持来源第二高分。在本研究中,以动物为中介变项,动物除了具有陪伴的功能,因动物具有实体,可以弥补宗教无法实际触摸的满足感。除此来自不同领域的老人,因个性上与生活习惯上较难调整,抑或身体上的障碍,因而产生了交友的困难,此时动物介入成为共同聊天的话题。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发现实验组在活动中音量增大、音调起伏、说话次数变多,显见正向情感明显波动。而动物方面则以其天性使然,容易使人卸下心防,在老人与动物互动的过程中,藉由抚摸,老人上肢明显运动,达到复健的功能,可由巴氏量表与正负向情绪前后测分数变化得到验证。
2.5 讨论
1) 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和人口学特质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宗教、婚姻状况和现在之经济来源并不会影响老人参加活动意愿,是否参加活动除了老人本身之意愿外,家人的同意与否扮演关键性角色。老人虽为独立个体,具有个人意志,但在家庭社会中,一般属于弱势族群,故其常无法拥有对于自我意向之决定权,且在访谈中发现,有些老人会参加活动,主要是家人同意或要求,因此他就参加活动。
虽然最后研究结果与本研究设计之人口学特质无很密切关联,但在以人为主的社会中,世界并非单由人类组成,因此如果加入动物,可以符合Dr. William Thomas于1990年发展出之健康照护概念——“Natural World”[3],如此可打破老人自觉于人外的籓篱,增进对真实世界的概念,促进人际关系之融合。
2) 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和生理健康的关系
Svedbrg等(2001)认为“自觉健康”是指个人对自己健康做整体性的评估[4];另外Bjorner等(1996)则提出“自觉健康”主要为个人对自己的健康情形,以个人独特的价值观评估而成[5]。经过六周后,实验组提升、维持或降低各占1/3;对照组大部分自觉健康持平(5位)没有变化,但从文献探讨,动物确实能影响老人之自觉健康,早自1998年Roenke和Mulligan即已提出动物可以增进人类情绪反应的效果[6]。
在生命征象及巴氏量表测量结果,实验组明显较对照组提升,但整体而言6周前后差异不大,没有明显变化,在生理功能上仍属于需照护级别。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对于提升老人自我照顾、减缓身体功能退化具有成效[7],但成效不明显原因,可能为研究期间太短及老人身体功能退化速度导致,故无法测出显着变异情形。但于活动纪录上,可以发现在短短1小时的活动时间中,老人平均之活动力诸如转头、视线跟随及手部及脚部动作明显增加。研究结果隐含着动物陪伴在老人生理功能肢体活动上,可以增加其个体主动之活动力,此点符合欧美研究将动物辅助应用于治疗上之结果[8,9]。
3) 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长期住在照护机构的老人,由于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与熟识的朋友,入住全然不同的地方再加上照护机构制式化的作息,容易导致入住者适应不良与产生孤寂感[10]。应用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并非狭獈地“利用”动物来增加人类健康,而是尊重人类的健康幸福“Well-being”状态[11,21]。以此观点,企图在枯燥的环境内,加入休闲活动营造出生活的感觉,转移老人专注负面情绪。因此在本研究为期6周的实验活动中,研究对象快乐的情绪与期待感随着参与活动次数的增加而强烈。这些愉悦源自于动物与研究对象抚摸、梳毛、握手、叫唤声和拍手的互动,因此表现在生活满意度与正负向情感出现频率测量数据。有动物陪伴之实验组其正向情感增加,负向情感降低,生活满意度增加明显改善高于对照组的原因。
动物陪伴确实能给予老人心理慰藉[21],透过与动物接触互动也会增加老人被需要的感觉,不会自觉生命无用、对生活没有期待、无聊等负面情绪,对于心理健康具有正面效益[12],可同时改善心理及生理功能[21]。说明宠物疗法具有增加社会相互作用、提供感情慰藉、成为自尊来源、减少忧虑感和增进独立的意义[13]、增加老人语言互动[14],激起老人的被需求感。透过动物和人类的交流,可以促进快乐、爱、安全和责任感的心理反应[15,16]。
4) 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和社会健康的关系
人际关系的维持能够让老人感到生活满足,并可调适晚年生活产生的压力[17]。根据研究结果实验组在社会支持行为5个面向中,情绪支持、社会整合、信息支持、实质支持均为向上提升,仅有尊重减少5分;而对照组不论在社会支持行为的任一构面,均呈现降低现象,尤其尊重更达降低28分之多,显示动物辅助休闲活动确能改善老人社会互动。另外在社会支持来源构面,虽然子女和医护人员仍为老人主要社会支持来源,但藉由活动6周后实验组得分变化,来自朋友(指同住照护机构之朋友)却增加了33分,在一群日常生活几乎不变的老人发生了此种人际关系的变化,得益于动物介入后老人拥有共同的话题,彼此之间语言互动明显增加,加深研究对象彼此间的了解,进而增加了生活中的同伴,因此也影响了朋友方面的得分。
社会支持在高龄期生活扮演重要角色,有时甚至能超越生理的不适感。动物辅助休闲活动对于老人之社会健康具有显着效益。动物帮助老人复健、活动并增加与他人互动的机会[18,19],建立人际关系,培养关怀社会的能力,降低对周遭人事物的冷漠,具有良好的成效。社会资源的丰富与人际的支持,可以成为改善支持来源与提升社会支持满意度之中介变项,亦可增加社会支持[20]。比较访谈结果,生活于照护机构之大部分老人对于未来通常已不抱希望,最常自觉老了就没有用、不要成为家人负担,也不愿打扰子女之家庭,故愿意住到照护机构以减少家人困扰。再加上传统观念子女通常要老人家享福、不要操心,习惯性报喜不报忧,久而久之可能加深老人对自身之无用感与社会疏离感。根据此研究结果显示,藉由动物陪伴,可增进老人对自身能力之信心、增加被需求感或增加家人互动之内容,并可提升社会互动能力。
3 结语
综合研究结果,生活于照护机构、护理之家或俗称养老院之老人,在文献探讨及访谈发现,最容易产生无聊、孤独、孤僻、忧郁、绝望、自怨自艾、不喜欢交谈、对外界丧失感觉及没有情绪表达等负面现象。透过动物人性化的陪伴和互动,可以增加老人的被需要性,连结老人与外在世界的反应、生理官能运动或肢体协调、提供情感交流、活化环境、降低焦虑、刺激语言反应、促进社会功能、刺激大脑记忆、转移对自身注意力至他人,增加聊天话题,扩大生活、社交圈,并可藉由期待固定时间动物的访视,增加老人的时间概念等益处。
而研究过程中,是否参与本活动之老人取决个人的兴趣与家属的意愿两大因素。尤其家属意见具决定性影响力,显示老人在高龄期通常丧失对生活的主导权。在这两个因素的运作下,46位住民之中仅有6位参加活动,而研究结果也表明6位老人在身心与社会互动方面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由此可知,设计能配合照护机构老人兴趣之休闲活动,或考虑进驻适宜家居性之动物,对老人身心具有正面的帮助[21]。因此本研究建议照护机构若能营造生活化氛围,纳入各种不同的生活属性,切实贴合老人需求,而不是专注于健康或维持基本生存功能,提供更多可以满足老人兴趣的休闲活动,将可使更多老人受惠并降低生理退化带来的生活不适感与心理压力及推迟社会退化。
注释
①该数据来源于2014年4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人口比例变化而呈迅速增加的趋势”。
②该数据来源于2020年4月21日台湾地区行政部门发布“台湾地区人口统计通报”。
参考文献
[1] 张素红.老人寂寞与自觉健康状态、社会支持之相关研究[D].高雄医学院护理学研究所,1996.
[2] 李美华,孔祥明,李明寰,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台湾:时英出版社,2004.
[3] 詹惠娟.国立成功大学职能治疗学系专题报告:宠物治疗[R].2004.
[4] Svedberg P,Lichtenstein P,Pedersen N L.Age and sex difference in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 for self-rated health:A twin study[J].Journal of Gerontology:Social Science,2001,56:171-178.
[5] Bjorner J B,Sondergaard K T,Orth-Gomer K,et al.Self-rated health:A useful concept in research,prevention and clinical medicine[M].Unscale:Rod & Form AB.,1996.
[6] Roenke L,Mulligan S.The Therapeutic Value of the Human-Animal Connection[J].Occupational Therapy in Health Care,1998,11(2):27-43.
[7] Decourcey M,Russell A C,Keister K J.Animal-assisted therapy: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complementary therapy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health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J].Dimensions of Critical Care Nursing DCCN,2010,29(5):211.
[8] Cole K M.Animal-assisted therapy in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heart failure[J].Americ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an official publication,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ritical-Care Nurses,2007,16(6):575-588.
[9] Willens J S.Animal-Assisted Therapies Are Becoming More Common[J].Pain Management Nursing,2013,14(4):183-183.
[10] 陈子萱,李百麟,黄志坤,等.老人孤寂感、生活适应与生活满意关系之探讨[J].危机管理学刊,2015,12(1):1-10.
[11] 叶明理.动物伦理与公共政策——动物辅助治疗(狗医师)[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2.
[12] 陈美如.中老年人宠物情感依附与社会支持之研究[D].台湾朝阳科技大学,2013.
[13] An Mháistir.Influence of Pet Ownership on self-esteem,Life satisfaction and Loneliness among over 65s in Ireland[D].Dublin Business School of Arts,2013.
[14] Greer K L,Pustay K A,Zaun T C,et al.A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Toys versus Live Animals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Dementia of the Alzheimer’s Type[J].Clinical Gerontologist,2002,24(3-4):157-182.
[15] Hart L A.The role of pets in enhancing human well-being:Effects for older people[M]// Robinson I(ed).The Waltham Book of Human-Animal Interaction:Benefi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et ownership.Great Britain:Pergamon,1995:19-31.
[16] Zink M R.Older people and attachment to things,place,pets,and ideas[J].Home Healthcare Nurse,1997,15(5):359-360.
[17] 朱妙英.台北县三莺区高龄者人际关系与幸福感关联之研究[D].台湾师范大学,2009.
[18] Velde B P,Cipriani J,Fisher G.Resident and therapist views of animal-assisted therapy:Implications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practice[J].Australian Occupational Therapy Journal,2005,52(1):43-50.
[19] Germone M M,Gabriels R L,Guérin N A,et al.Animal-assisted activity improves social behaviors in psychiatrically hospitalized youth with autism[J].Autism,2019,23(7):1740-1751.
[20] Carmack B J.Companion animals:social support for orthopedic clients[J].Nursing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1998,33(4):701.
[21] Hege L.How do animal interventions promote well-being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D].University of Twente,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