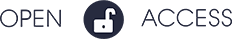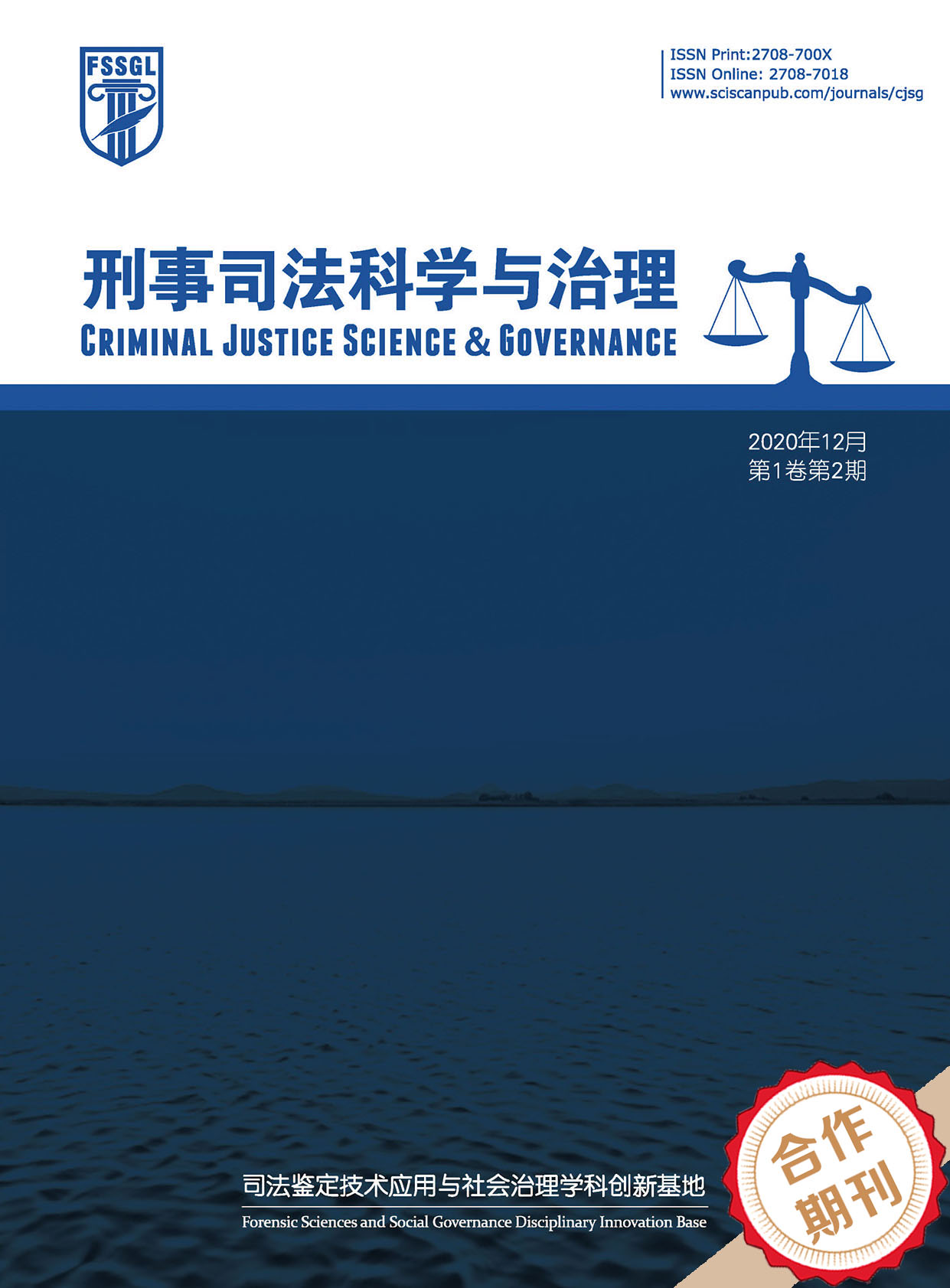Criminal Justice Science & Governance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核心能力建设与国际比较:研究进展与思路
Core Capacity Building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Research Progress and Ideas
- Authors: 闫平¹²* 戚建刚¹ 张琦¹ 祁毓¹
-
Information: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2. 司法鉴定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学科创新基地,武汉
-
Key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Core competencies; Institutional system; Mechanism desig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核心能力; 制度体系; 机制设计; 国际比较
- Abstract: The building of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s the key for countries to deal with major public health security risks.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riggered a major public health safety risk ev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have become the key for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deal with major public health security risks. Based on actual needs, this paper aims to build a well-documented and effect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s, clarify the basic structur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 structure of core capabilities, and establish a general dynamic standard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 data and a variety of methods system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main nation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status of the core competence. Based on these work above,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level of core competence of the state, and therefore identify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core competence. Finally, this paper refines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build a replicable and generalizable core competence improvement path in a general sense.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建设,是各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的关键所在。 新冠肺炎在中国和全球爆发,引爆了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提高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的关键所在。本文立 足现实需求和文献进展,旨在构建一个论之有据、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分析框架, 厘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架构和核心能力的结构,建立一般性的动态标准评价体系; 采用多种方法系统评估和比较主要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核心能力的状况,分析中国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核心能力所处的水平状态,甄别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核心能力 的优势和短板;最后,提炼总结各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经验,构建一般意义上的可复制 可推广的核心能力提升路径。
- DOI: https://doi.org/10.35534/cjsg.0101001
-
Cite:
闫平,戚建刚,张琦,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核心能力建设与国际比较:研究进展与思路[J].刑事司法科学与治理,2020,1(1):1-29.
https://doi.org/10.35534/cjsg.0101001
众所周知,新冠肺炎在中国和全球爆发,引爆了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纵观人类历史爆发的各类风险事件,人类所面临的风险类型越来越多,而传染病由于其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指数化的扩散性和超强的叠加效应,使得人类在时空等维度遭遇了极大冲击和挑战。从根本上讲,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成为各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的关键所在。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及时补救和反应,在“抗疫”过程中重塑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展现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核心能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建设,是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关系到国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分为四个阶段: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监测与预警阶段、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恢复与重建阶段。历史经验表明,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在应急管理系统中担任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预防与准备的完善能很好地减轻后面几个阶段的压力,为公共卫生事件的顺利应对奠定坚实基础。早期识别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是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并降低突发事件影响的关键所在。2003年SARS发生以来,CDC建立了传染病与突发公共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形成了纵横贯通的信息报告网络,显著提高了疫情报告的及时性、敏感性和准确性,使得我国对传染病疫情的监测、报告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基本上实现了各种信息报告的直报、实时查询。同时,有效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公共卫生体系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硬核”,如何把损失和危害降到最低,需要精准科学到公共卫生资源和其他配套资源的精准配置和匹配。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事件的突发性、空间的群体性、危害的严重性等特点,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置身其外,并且对此都不能置若惘然。由于制度背景、资源禀赋以及卫生事件遭遇的时间和程度差异,各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基础、治理能力和管理体系都各有所长以及存在明显短板,置身于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中,加强合作,取长补短,精准施策,不仅对于应对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有裨益,也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突发性事件提前埋下“伏笔”。
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也是人流、物流等高度发达的社会,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具有多样性、隐蔽性和普遍性,人类目前的科技手段依然难以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但国家通过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核心能力建设,通过法制化方式来提升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代价来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在第一时间阻止它们演变成极端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由此我们需要一种权威高效的公共卫生管理应急能力体系。目前,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研究仍然停留于“事务”层面,实务界与学术界的交流不足。此次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信息处理和疫情预防不及时的问题,同时疫情的变化和防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可以有效地缓解早期信息处理不及时所带来的弊端,核心能力的建设一个时空动态的过程,需要及时总结以往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因此,通过比较研究,引入先进国家的理论资源,有助于形成符合国情的公共卫生应急理论体系。应急管理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方面,行政权的规范运行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从整体上思考行政应急的规范化、制度化问题,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应急法治理论。在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公共卫生风险日益加深,相关应急管理工作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通过对比各国相关体制机制经验,能够加深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联理解,也有助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体系。
1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核心能力建设研究进展
1.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1.1.1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核心能力的评价与比较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评价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的评价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评价的准确性及有效性对于成功进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至关重要[1]。各国对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评估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
(1)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核心能力的评价维度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的国家。州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评价体系(State Capability Assessment for Readiness,CAR)和公共卫生准备和反应能力清单(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Capacity Inventory)是美国早期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评价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是美国评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核心能力的重要工具。前者是由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和国家应急管理协会(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ociation,NEMA)联合开发的国家评估标准,使州、领土或偏远地区能够判断其应急管理的准备情况和能力;后者是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开发的,用于帮助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评估州应对生物恐怖主义,传染病的爆发、公共卫生威胁及突发事件等方面的能力。州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评价体系评价的维度较为广泛,主要从法律、计划、训练、公众教育信息、通信和预警、危险识别和评估、风险管理、资金管理、物资管理、行动程序、指挥控制协调、演习、后勤装备13项应急管理职能方面进行评价(FEMA and NEMA,2000)。公共卫生准备和反应能力清单将评价的维度划分成6个重点领域,包括规划和评估、监测与流行病学、实验室能力、传播与信息技术、风险传播与健康信息传播以及教育与培训(CDC,2002)。2013年起,美国进一步推出了“国家卫生安全应急准备评价指数”(National Health Security Preparedness Index,NHSPI)并每年持续更新。该指数综合多种来源和角度的举措,为整个国家和各州的卫生保护措施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评价视角。该指数分为卫生安全监测、社区规划和参与协调、事件和信息管理、健康保健服务、对策管理、环境和职业卫生6大方面,并细分为19项139个具体测量指标。
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或组织也逐步制定了相应标准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进行评价。欧盟制定的“评估卫生系统危机管理能力工具包”(Toolkit for Assessing Health-System Capacity for Crisis Management)将评估内容划分为领导和管理、卫生人力资源、医疗产品疫苗和科技、健康信息、卫生筹资、卫生服务提供6大方面,并分解为16 项核心评估内容及51个评估指标,用于评估欧盟成员国的卫生应急准备情况。2002年,针对日本防灾以及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的问题,日本消防厅和防灾与情报研究所牵头负责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次“地方公共团体之区域防灾能力及危机管理应对能力评估研讨会”,会议设定了日本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的内容,包括:灾害情况的假设、危机的掌握与评估、整顿体制、居民间的情报流通、情报联络体系、器材与粮食储备管理、减轻危机的对策、教育与训练方式、应急水平的维持与提升以及应急反应与灾后重建计划等。我国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中国卫生行政部门应急能力评估”工作,通过问卷调查全面了解我国卫生应急能力现状,将卫生应急能力指标体系分为体系建设、应急队伍、装备储备、培训演练、宣传科研、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善后评估8个一级指标,并细化为34个二级指标和81个三级指标。 在国际上,鉴于全球灾难性生物事件冲击的风险增加和国际资金在防疫方面的重大缺口,2019年美国削减核威胁倡议组织(NTI)、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HU)联合经济学人智库(EIU)和国际咨询公司共同开发了全球卫生安全(Global Health Security,GHS)指数。这项评估从预防、查明和报告、快速响应、卫生体系、遵守国际规范及风险环境6个方面开展,并细化到了34个指标、85个子指标和140个问题,为各国诊断卫生安全体系并发现问题和提高能力提供了指南。
在该领域,相关研究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Nelson等[3]界定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核心能力评估应满足的原则性条件,即适用、可靠、可行且能够发挥效用。Donabedian(1966,1980)以及Turnock和Handler(1997)从结构、过程、输出以及结果4个维度构建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评估的概念框架。Handler等(2001)在上述框架的基础进行了拓展,构建了一个囊括宏观环境、任务、结构能力、过程和结果5个维度的评估模型。尽管不同研究可能采取不同的衡量方法,但上述框架模型奠定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评价的基础。Nelson等延续了上述研究,提出在结构维度中应侧重于对人员、设备、训练、领导组织能力、计划、训练及纠正措施等方面进行评价[3];在过程维度中应注重对活动执行情况的评价,包括大规模预防、隔离、检疫、公共交流等;在结果维度中不仅应关注受灾或受影响人群健康的维护和恢复,还应该关注系统是否对发病率和死亡率产生其预期的影响以及是否能够有助于帮助结构和过程维度进行决策。Li等[4]以及Sun等[5]在上述概念模型的基础上,选择疾控中心人员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员工比例、政府资助情况、一般机构支出的资金百分比、每名职工的工作范围以及设备运行效率等作为评价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选择服务的完成性指标来系统度量公共卫生的服务能力。其他的一些研究也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构建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的评估框架。Hu等[6]的研究将能力评估理论和应急管理理论应用于评价体系的构建中,强调需要从个人、组织以及系统三个维度进行具体评价,并建议划分为预防、准备、应对以及恢复4个功能模块设置对应的评价指标。王晓东等从准备、监测和预警、应对及事后评价4个阶段设计了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的评估指标[7]。准备阶段包括预案、队伍人员以及物资储备评价;监测与预警阶段包括监测预防、预警能力、突发事件报告等方面的评价;应对阶段包括应急响应、指挥协调、事件影响、现场需求、现场防护、事件探因、伤员救治、现场控制、媒体应对、公共指导以及社会综合管理等方面的评价;事后阶段包括人员安抚、影响综合评估、事后评估制度建设等。Mccabe等构建了一个更为普遍和适用性的框架[8],从“准备”“意愿”和“能力”三个维度评价公共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核心能力。
(2)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核心能力评价的技术方法
尽管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核心能力评价容易受到诸如人为判断误差、数据和信息可得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以致难以准确评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核心能力,但既有研究也开始逐步开发一些评价技术来提高评价的准确度。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开发出很多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评价的技术工具,如圆桌演习、调查问卷等[9]。在诸多评价工具中,应用范围最广的是问卷调查法[10],问卷调查法是基于学者或者研究机构的直接思考,识别出不同情境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应具备的核心能力,构建应急管理过程的核查清单,表现出精细化和情景化的特征。进而基于问卷调查法的评价技术具备识别主体感知的特征。由于公共卫生管理应急体系核心能力评价既重要又亟需评价者的充足经验,因此头脑风暴、专家访谈、德尔菲法、文献分析法等制定核查清单或案例研究的方法成为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核心能力评估的主要方法。随着建模技术的不断发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开始涌现。层次分析法在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韩传峰和叶岑通过建立综合层次分析模型,量化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包括组织体系、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资源保障和事后总结等方面。杨青等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建立了基于过程管理的城市灾害应急管理综合能力评价体系,采用综合评价表对政府部门的应急反应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田军等的研究通过建立能力成熟度模型,量化评价了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一些模型技术也开始用于缓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评价中的主观性偏差,如模糊集的路径,人工神经网络,人工社会网络、计算实验和并行执行(Artificial societies,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and Parallel execution,ACP)等建模方式。
1.1.2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核心能力的影响因素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其核心能力的辨析,影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核心能力的关键因素包括制度、参与方、应急管理系统三个主要方面。
(1)国家制度层面及其顶层设计
我国政府在加强应急管理中,围绕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即“一案三制”),构建了应急管理体系的核心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管理作为管理公共危机的主要手段[23],应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一套多层次、多领域、动态管理的应急预案体系,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和非常态相结合的预案体系[24]。尽管“一案三制”的综合应急管理体系符合国情、基本可行,但也有两大弱点。一是没有目标规划,无法评价效果;二是全灾种管理与全过程管理难以兼容[25]。同时,我国当前的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形势依然严峻,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急管理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缺陷,并且从此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也可看出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并不完善,因此,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化应急法律体系、创新疾病监测与预警系统、改善应急组织结构、加强公众应急宣传教育等已成为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的关键因素[16]。
(2)多方协作共同参与
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不仅仅需要地方政府起主导作用,社区和社会组织也将在应急管理中起到积极作用。Waugh 和Streib提出[28],协作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必要基础,而且作为“强政府”国家,中国需要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国家的应急管理[29]。Henstra提出,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制定必要的政策和具体程序来有效应对社区突发事件及其后果,那么在应急管理中将发挥关键作用[30]。我国学者谷春江(2019)提出,作为地方应急管理的直接执行机关和践行机构,地方政府在应急管理中担当首要的责任。除了地方政府之外,Harris和Clements也指出,有效应对大规模公共卫生威胁需要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协调一致的努力[20]。尽管社区协调需要沟通和规划预防措施,以应对严峻的灾难威胁[31],然而对于负责确保公众对其健康和安全的反复威胁做出有效反应的政府官员而言,如何组织社区响应是一个主要问题[32]。反复发生的威胁和警告可能会导致社区麻木,导致低估和准备不足,因而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使灾后恢复速度变慢。可见,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对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而言极为重要,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是实现整体性治理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李菲菲和庞素琳也指出,社区作为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前沿阵地,加强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对于突发事件的预警、减缓、处置和恢复具有重大的意义。
(3)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的有效性
尽管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和响应系统对减轻所有突发事件对人口健康的影响至关重要[38],并且诸多证据表明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能够更好地保障公共健康安全,但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仍对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造成了严峻的挑战[5]。鉴于现有的公共卫生系统在法律和组织上极为复杂,导致了不同地方政府或地区基础设施存在极大差异,因此构建具有普适和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是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核心能力的关键性手段[39]。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因素之外,社交媒体、信息技术等现代化的方法也逐渐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29]。
1.1.3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核心能力的治理效应
(1)提升预警能力,防范重大风险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戴伟·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2006)提出了“成为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非治疗”的政府治理公共危机方式的理念。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可以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从而有效预防各种危机,以此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实现社会的正常稳定运转以及协调可持续发展[40]。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监测预警系统的构建可以有效提升国家面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和防范能力,防患重大风险[41],有效降低各种灾害发生的危害程度,减少民众伤亡和财产物资损失[38]。在全面整合的应急管理模式指导下,按照“长期准备、重点建设”的要求,重点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准备、预备和预警等基础性工作,做好日常的应急培训、演练以及其他各项基本制度建设,对提高政府的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和防范能力,使国家应急管理工作成于规范具有重大促进作用[42]。美国全国公共卫生信息联络系统建设的先进经验也从实践层面表明:建立相对独立、垂直管理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在疾病爆发与大规模流行前启动预警方案,可有效加强对可能疾病的症状监测,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赢得时间,从而最大程度的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27]。
(2)提高应对效率,降低治理成本
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个阶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指挥协调系统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专门和核心协调部门,有利于保证各个职能部门之间高效的协同运作,降低治理成本,增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43]。同时,有效的多元参与危机管理模式必须基于各行动主体在应急管理中拥有合理的利益。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应急管理体系中多元参与的危机管理模式通过多元参与主体的主动参与、自动响应、自愿合作可以加强协同合作,提高应急管理措施的实施效率[44]。在应急治理决策、指挥、执行、反馈等于一体的权责体系和协作机制下,基层执行主体将及时向指挥中心报告相关信息并执行指挥中心命令以合理调配医疗资源,缩短城市应急管理链条,提高应对效率[45]。通过梳理美国、日本和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制度和模式,尤其是在其应急物资储备与发放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应急物资快速反应系统,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体系可以在疫情爆发时迅速做出反应,保证疫情期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及时需求[27],同时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有助于鉴别危机发生诱因、完善疾病监测、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和实验室鉴别诊断网络,提高快速反应、准确判断、积极应对的能力[46]。
(3)优化资源配置,科学财政决策
预防为主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可以大幅度降低过高的事后救济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47];而灾害发生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中覆盖事前预备、事中处置到事后补偿的全过程风险分散机制可以提高应急财政资金的管理[48]。但危机管理通常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就能够有效完成的,在很多情况下,它都需要涉及多个部门,而且危机事件越复杂,涉及的政府部门越多,协调的交易费用就越高。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可以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降低这种交易费用,进而提高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49]。基于治理视角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居民、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整合资源,构建一个开放、协作、功能互补的治理网络,使得各主体能充分互动、相互博弈、取长补短,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37]。
(4)提高问责效率,提升政府公信力
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提供了突发事件绩效评价的基准,方便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应急管理资金使用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从而保证资金接受主体受托责任的履行[30]。同时通过监督和评价基准,政策制定者可以快速评价防控资金物资运用的合理性和成效,有效衡量接受政府投资的各级主体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执行能力,强化行政问责[3]。王薇和曹亚[22]在准确剖析我国突发事件频发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合理的应急管理体系对考察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评价当前政府应急管理水平,提升我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和治理能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应急管理体系中面向过程的评估方法,可以更好地反映政府在应急反应处置过程中的综合管理效果,明确管理的薄弱环节,并建立针对性的改进方案,从而使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得到逐步提升和持续改进[19]。
1.1.4 文献评述
通过对上述文献思考和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思考与启示:
第一,国外的实践和研究较为系统和成熟,为我国公共应急管理评价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借鉴。就国内实践及研究而言,其发展相对滞后,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评价体系。因此,如何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评价体系则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既有的评价指标的研究存在维度单一化以及没有考虑各层次指标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的问题。一方面,多数研究仅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的阶段来构建评价指标,忽略了不同个体或组织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的影响力度以及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当前的定性识别和分类方法难以反映不同评价维度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依赖。因此,有必要在公共卫生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内嵌入不同应对主体作为观测对象,从动态演化互动的视角,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进行“循环化、全流程”的评价。
第三,当前公共应急管理评价的研究多是问卷调查和访谈以及通过个案的探讨进行阐释,缺乏大样本的案例研究。专家调查的可信度取决于专家渠道的选择和有效问卷的数量,个案的探讨尽管具有启发性但面临一般化的挑战。未来可以借助更为精准的技术模型通过对各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大样本案例研究,以验证个案研究的准确度,纠正人为推断的误差,进而增加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评价的准确性和普适性。
第四,当前研究缺乏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综合考量和对治理效应的准确评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涉及主体众多,影响因素广泛。不同的研究已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仍未将相关影响因素综合置一个系统的框架内予以考量,存在重叠和缺漏的可能。因此,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视角,识别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关键影响因素并采用技术手段对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度进行量化是识别影响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核心能力关键因素的一条可行性路径。其次,当前鲜有研究科学、准确地评估量化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核心能力的治理效应,因此如何利用现有的技术方法识别并准确评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核心能力的治理效应是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2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基本架构与组成要素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见图1)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治理工作,相关的制度、机制和体制要素多样而丰富,且相互之间又具有密切关联。其中,制度提供应急管理的基本操作模式,机制提供应急管理的基本推进路径,体制提供应急管理的基本运行架构。完整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至少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完备的制度体系,二是完善的组织体系。在组织体系执行具体制度的过程中,会形成具体的管理机制。通过对具体机制进行不断的完善和优化,制度和体制的磨合程度会不断提升,最终不断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治理能力。

图 1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Figure 1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1)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体制建构。体制侧重从基本架构层面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供主要框架。具体而言,需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行政与专业的关系、应急与常规的关系、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体制建构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之处在于既要发挥中央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保持中央强有力的整合力,又要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至于消极被动等待中央决策;条块关系的关键之处在于,协调条块之间的信息沟通、职责边界,防止出现因条块关系不顺而导致的推诿卸责、不积极作为等不利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问题;行政与专业关系的关键之处在于,赋予公共卫生专家系统在应急决策、信息传输等方面的话语权,协调处理好专家系统与行政系统在决策中的权力职责关系,防止行政系统干扰专家系统基于专业科学知识做出的判断;应急与常规的关系所要回应的主要是,一方面要保持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重视度,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协调处理好应急管理与常规管理之间的关系,将常规管理中的管理负荷保持在适合的程度内。而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处理,重点在于要正视国家正式体系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不足,积极引导、发挥社会主体、市场主体的作用,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提供更为丰富、多样、有效的资源和方式。上述几个方面关系的处理,都需要汇集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展开布局。
(2)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机制运行。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机制,这些机制之间相互连接、协调配合,共同保障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信息传递机制。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没有准确、及时的信息,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在此方面,需要重视从职责权限、技术手段、组织体系、民意汲取、宣传报道等方面探索构建具体层面的实施方案,从而保障有关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的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到相应决策层,并且保证各个层级之间不存在虚报、瞒报、漏报情况。应急决策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有应急性,这对决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能够做出正确决策,还要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恰当的价值权衡选择。在保障各个层级、各个部门之间信息传递通畅的同时,要赋予专家系统、地方政府更大的临机决策权。执行监管机制。有关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决策不仅要正确作出,还要能够切实执行落实。在此方面需要注重人大的监督作用,特别是相关执法检查,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之间的衔接。人员调配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需要多方面、多领域人员参与,需要完善相应的调配机制(尤其是军队人员调配、专业领域人员调配、公务人员调配),充实公共卫生应急的人员保障基础。公众参与机制。公共卫生应急,尤其是重大公共卫生应急,往往需要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发挥群众的参与作用。在此方面,要注重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参与应急信息传输、救助救援,完善志愿者工作机制、慈善组织运行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在此方面的重中之重在于,要完善相应方案,充分调动社会主体、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将社会资源、市场资源有效、有序地整合进应急管理体系中,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方方面面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既要注重保障专业救助方面的资源供给,也要重视保障民众日常生活层面的资源供给。应急舆情处置机制。这方面的机制非常重要,对应急决策的作出、应急执行的实现、社会恐慌感的缓解或消除等方面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重点在于准确识别舆情、有效及时回应舆情,特别是要能够把握移动网络自媒体时代的舆情产生于传播的特点,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舆情处置机制。
(3)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制度设计。这方面的主要内容在于,要能够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体制建构和机制运行体现在法律规范之中,以法治化的方式保障实现。也就是说,要系统深入探究和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法源基础。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涉及法律部门多,几乎现有各主要法律部门中均有相应内容。因此,一方面要系统详细梳理既有法律体系中有关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索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法律规范,尤其是要注重在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部门中健全相应的制度规范。通过健全相应的法律规范体系,准确界定国家权力主体的职责边界,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合理划分社会成员、市场主体在公共卫生应急中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各方面主体在公共卫生应急中的职责的法治化。
(4)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能力建设。体制、机制和制度,最终都要体现在能力层面,只有能力的提升才能证明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有效性。能力所要解决的是要将公共卫生应急的体制、机制、制度效能体现在具体主体的行为中、体现在应急管理的具体过程中。换言之,体制、机制和制度,主要是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提供框架结构和行为规范层面的外部条件。若要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能力,除了体制、机制和制度之外,还需要重视知识、技术、心理、意识、观念等方面的完善和充实。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能力涉及面非常广泛,概括提炼来看,这样几个方面的能力是核心能力:应急预防能力、应急准备能力、监测与预警能力、应急处置救援能力、恢复与重建能力。这几个方面的能力,在前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各个主要环节或领域均需有所体现。在这几种核心能力之外,还有其他具体类别的能力。
3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核心能力评价体系
3.1 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的能力
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具有突然性、复杂性、破坏性和不可预测的特点,及时甄别、有效掌握、科学处理,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社会稳定。公共卫生时间应急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是对一个组织或系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时间的综合能力的评价。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薄弱环节或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应急能力持续改进和满足应急需求。
确定三个核心能力:预案准备能力、机构应对能力、物资储备能力。在预案准备能力方面,考虑预案的完备性、可操作性、维护和修订、培训与演练情况。在机构应对能力方面,考虑应急组织机构建设、应急队员专业构成与技术水平、培训和演练计划方案完成情况、应急培训实施和培训咨询归档情况。在物资储备能力方面,考虑应急物资储备、场所安全防护、应急现场处置情况(见图2)。

图 2 预防与准备阶段的核心能力
Figure 2 Core competences required in prevention and preparation stages
3.2 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的能力
从“人”“财”“物”和救治效率四个方面来考察典型国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的能力,“人”主要考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护人员的供给能力;“财”主要考察当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能提供的资金保障能力;“物”主要考察医护物资的供给能力。
3.3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监测与预警能力
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原则,建立一个覆盖多种事故类型、多部门、多环节的指标库。在信息获取阶段,信息获取能力重点考虑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全面性、以及信息质量;对于信息甄别与危害评估能力的评判,主要考虑信息甄别人员的经验、专业水平、综合素质,对所采用的信息甄别以及案例推理方法以及程序有效性、科学性进行评估;在预警能力评判方面,主要对预警报告上报的及时性以及上级部门反馈的及时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监测与预警阶段能力影响因素具有高维特性。首先,监测与预警能力与公共卫生事故的性质直接相关。事故的性质包括事故类型、事故的复杂性、持续时间、严重程度等。其次,监测与预警能力与监测信息的获取、处理、上报与反馈机制有关,也与预警与监测相关人员的工作经验、心理状态、技术水平与素质与品德。再之,与各级政府制定的相关制度与法律法规相关,与政府部门对舆情的监测与控制措施以及对信息上报人员的激励与惩罚机制直接相关。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监测与预警工作具有多方面的复杂性:(1)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监测与预警能力与宏观的政府制度、法律法规直接相关,也与微观的组织、个人的能力、经验等因素直接相关。(2)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应急管理监测与预警即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责,信息的来源与企业、医院、公众也有直接的关系。(3)过程的动态性。监测预警工作本身就包含信息获取、信息甄别、灾害评估、预警报告发布等多个阶段,同时,监测与预警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持续改进的反馈过程。可以综合应用系统动力学、多主体仿真等方法,建立多视角下的应急管理监测与预警能力路径提升综合仿真模拟平台:在宏观层面,借助系统动力学模型建模制度因素、组织因素对监测预警能力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基于多主体仿真,描述个体之间的交互与博弈。通过设置不同的事故场景,测试复杂影响因素对应急监测与预警能力的影响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见图3)。

图 3 监测与预警能力要素关系模型
Figure 3 Relational model of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capability elements
3.4 恢复和重建核心能力评价与比较
应急处置阶段的活动结束后,并不意味着突发事件应对过程的结束,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突发事件应对的后处理阶段。突发事件消除后的恢复,是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的最后环节,它主要指受到损害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的恢复,受到破坏的国家法律秩序的恢复,以及受到损害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恢复。在这个阶段,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至少能弥补部分损失和纠正混乱的机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恢复期是指突发事件的危害性明显降低、危害范围缩小,人们开始采取措施消除突发事件后果,恢复社会正常状。市场(企业)恢复与重建能力评价与比较、社会(公民)恢复与重建能力评价与比较、政府(公共部门)恢复与重建能力评价与比较。
4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国际比较与经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许多方面都不是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可以有效应对,而是需要开展国际合作。而且,不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也并非只是发生于一个国家,而是会在多个国家,甚至全球范围都会有所体现。因此,设计和运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越来越需要有国际视野。在此方面有三点尤为重要,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其一,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方面的做法、经验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或教训。其二,不同国家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方面的合作如何开展,既涉及常规状态下的合作交流,也包括应急状态下的合作和支持。目前而言,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需要在理论上更加重视对域外经验比较的研究。其三,不同国家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有一定的共性,但是由于各国国家体制、社会基础、卫生医疗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存在差别,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也会有诸多不同之处,因此在域外经验比较中,既要重视学习借鉴,也要充分考虑到各国国情基础与现实条件的差异。
最后,美、日、意大利、中国等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模式比较研究。
(1)美国模式。在制度上,美国应急处置相关立法较早,形成了以联邦法律、总统命令以及政策指南为主体的应急处置制度体系,各州也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此外,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作为美国和总统指令的细则制定者,在应急响应、响应方式、职能明确、部门协作等方面制订了具体的政策及相关指南。在机制上,美国在1979年以前主要采用“分灾害、分部门”的单一灾害应急管理模式;但1979年之后开始试行以 FEMA为核心的综合性突发事件管理模式。此后,美国逐渐发展出包括“联邦—州—地方”的三级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具体分为纵向主系统和横向子系统[27]。其中,纵向主系统包括隶属联邦政府的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HHS)、美国州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和地方性卫生部门。横向子系统则分为全国公共卫生信息联络系统、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诊断系统、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系统、全国应急物品救援反应系统四个部门。
(2)意大利模式。意大利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具有以下几大特色:政令措施的法治形式;以专业机构和专业意见为引领,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建立疫情前后的应急管理制度;建立“预防—指挥—医疗—干预”四大板块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制度。通过前期预防,疫情指挥和医疗,后期干预的制度措施,形成保意大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意大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与行政体制是密切相联。2005年,欧盟设立了“欧洲疾病控制中心”专用于判断欧盟领域内的安全风险,用于通报安全信息、协调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安全管理措施,以及协助与指导欧盟成员处理本领域内的安全风险。虽然意大利本国的应急指挥系统是应急管理措施的主要决策者与执行者,但在实际运作中也通常会参考来自欧盟机构的指令与建议。意大利应急指挥系统调配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全国的所有行政机关与自治组织。诸如,国家医疗服务团体;国家科学研究团队、国际技术服务团队;火警、交通警察、宪法等警察成员、军队,主要负责社会的秩序,协助医疗应急管理措施的执行等。意大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预防体系是基于“辅助性原则”建立的,即该体系主要用于辅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具体展开。在该体系中,制定预防计划是核心任务,其制定者主要为民防部门。同时,由于所定计划应当具有可操作性、层次性、一定的灵活性,通常也需要听取参与者的具体建议。而且,随着对应急情况知晓程度的加深,以及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发展变化,该应急方案还会进行调整。此外,为了能够真正意义上地开展这项活动,该体统也负责收集、分析、解释各项数据的任务,以准确地制定预防计划。由于引发公共卫生安全的事由各种各样,因此意大利负责预防各项潜在危险的机构亦是五花八门,各成体系。为此,意大利建立了危险监测与危险信息共享的二元机制。如在检疫监控方面,国家实验动物中心在全国设有10个分支机构(IZSLR),有90多个省级分支机构,以进行动物屠宰检疫、提供动物疫苗、起草年度免疫、疾病监控报告。在监管机构获得相应信息后,就会进行横向与纵向通报给相应的负责部门,以尽可能快速地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一般而言,这些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信息都会汇总到各个相应辖区的卫生部门与民防机构。在意大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国家医疗服务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意大利的医疗服务体系共分为三级: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区级医疗服务体系以及地方医疗服务体系,意大利政府专门设立“卫生部”以专门负责管理意大利境内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的医疗机构则主要可以分为地区医院与大学医院两种,并分为三个等级。当然,这种分类并不代表医疗水平的高低。各地方的医疗机构分别归属于意大利卫生部下设的地方医疗局与大区医疗局,医疗局对医疗机构进行管理与监管。其中,卫生部负责制定总体的规划,包括医疗投入、制定符合欧盟政策的购买器材和医疗器械规则,负责改善全面健康状况。大区医疗局与地方局分别负责各自管辖房内的医疗事务管理。在意大利的医院内部设有急诊接受中心专门用于处理日常的紧急医疗事件。其急救体系由公共医疗体系与救护志愿者协会所构成。一般而言,负责急诊电话的人员一般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在救济中心的每个操作台前都设有专门设备,装有雷达定位体系、患者病情基本信息表格,从而可以在短时间内根据病情轻重程度以及地理位置的远近派出相应的急救交通工具。为防治传染病的扩散以及所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对于传染病的疑似患者,也应通过急救服务前往医院,以获得诊断与治疗。疫苗干预措施素来是公共卫生学中对于预防传染病传播的关键手段。不过,该手段主要是用于预防阶段,在没有出现紧急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病之前,其数量有限且难以获得具有针对性高的疫苗。为避免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发生,意大利医疗预防侧重于将预防和治疗理念渗透到了各级医疗部门,各级医疗机构则在内部设置疫苗接种与肿瘤筛查的服务场所与接收站。同时,法律规定达到法定月龄的儿童必须接受特定疫苗的接种,儿童疫苗的接种情况也被涵盖于各个地区的疾病监测体系之中,以保证公共卫生的安全。此外,意大利还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个人健康体检体系,要求人们进行定期检查,以预防疾病。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启动后,各医院按照各自的职能与应急管理安排救助患者。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往往独力难撑。为此,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需要与私人诊所、私人医疗机构、各个高校之间进行合作,统筹利用社会可用的医疗资源。如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所需专业人员不足,为应对紧急情况,医疗部门可以聘用社会志愿者、私人医生、退休医疗人员以及即将毕业或者已经完成相应职业培训的人员,使他们都可以参与到医疗救助服务中来。如果医疗设备资源短缺,政府医疗服务的管理部门则可以通过签订合同或采用征收征用的方式利用民间医疗资源,但要求政府的具体举措公平合理,并应当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相关的是应急医疗科研体系,对此部分意大利高校的研究中心与地方及国家卫生部设立了“卫生高等研究院”。卫生高等研究院下设了环境暨健康心血管、内分泌代谢疾病暨老化、传染病、神经科学、肿瘤暨分子医学、食品安全、营养暨兽医公共卫生等多个研究部门。在这些部门之下,有将近20个研究中心分别进行公共卫生实验等研究活动,以及掌握公共卫生情况和提供相应的咨询工作。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风险评估、相关技术性难题的处理方案也多由该机构提出。意大利的部长委员会以及民防部门在进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部署与执行时,也会充分听取与尊重来自该部门的专业意见。
(3)日本模式。199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了《厚生劳动省健康危机管理基本方针》,确定了日本包括感染症在内的公共卫生健康危机管理体系。方针中确定的“健康危机管理”是指,由于医疗用品、食物中毒、感染症状、饮用水等原因危害到国民生命健康,对此事态采取预防、防止扩大传染以及治疗等相关工作,均属厚生劳动省所管辖。健康危险信息由于医疗用品、食物中毒、感染症状和饮用水等原因直接危害到国民生命健康的相关信息。“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是医政局,医药与生活卫生局、食品安全部以及劳动基准局安全卫生部。
关于收集健康危机信息,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设置了有关健康危险信息收集窗口,致力于大范围收集并分析信息。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获得难以获取的健康危险信息,健康局在各个都道府县,医生会等的协助下,活用厚生劳动行政综合系统,通过卫生站等收集信息。关于对策决定的过程,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对健康危机管理采取决策时(包含还没有具体对策只有大纲的情况,下面也是一样),根据其重要程度,在向厚生劳动大臣传达后在进行决策。除此之外,在必要的情况下与其他相关部门长官进行协商。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在特别重要的健康危险信息和其对策的决策上,要向内阁总理大臣传达。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在决策与健康危机管理相关方案后,在该危险变没有之间,根究情况,加强监视体制,积累必要的信息和相关知识,顺应决定对策的诸多前提条件的变化,对于政策进项修改。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应适时适当地对于决策进行调整,适当整合决策的诸多前提条件和判断理由的相关资料。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在进行与健康危机管理相关的重要决策时,应快速地将其公开,同时在信息不明确的情况下实行决策时,以此为前提的信息和知识、重要因素、制约条件等也应整合,并公之于众。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以健康危机管理相关对策为基准,指导行政机关,相关团体落实时,除去紧急或者迫不得已的情况之外,要写相关文书。在紧急和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没有文书指导时,也要通过加急写出文书,明确指导的相关内容。
关于健康危险信息的提供,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要设立提供健康危险信息及有关对策的窗口。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应当通过媒体机构、政府公告以及先进的信息通讯网络向广大公民提供国内外涉及健康危机管理的信息,并通过医疗系统向有关方面提供信息。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要灵活运用“厚生劳动行政综合体系”,及时向地方部门、都道府县、卫生站、地方卫生研究所、国家医院组织的各类医院提供重要的紧急健康危机管理的信息以及有关对策、治疗方法等,必要时,可以召开各都道府县干部负责会议。健康危机管理负责部门,在完善医疗机构的治疗方法及有关信息基础时,对于重要的紧急健康危险信息及治疗方法等的信息,要灵活运用“紧急通信”等手段,及时向医疗机构提供有关信息。
5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核心能力提升路径与启示
当代突发事件管理理论认为,每一个突发事件都会经历潜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周期,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不应该局限于其生命周期中的某一个阶段,而应当着眼于全过程,即根据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政府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的、全过程”的管理模式。据此,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核心能力的建设也应当覆盖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过程,从而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的能力建设、监测与预警阶段的能力建设、 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的能力建设与恢复与重建阶段的能力建设,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性的能力建设过程。
5.1 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的能力提升路径
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一阶段,是防患于未然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
(1)政府与社会合作能力: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助,建立多方位、分权自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机制,提高全社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2)制定和更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能力:为了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政府有必要制定并更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确保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开展处置工作。
(3)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源的监控能力: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等组织能够迅速发现和确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险区域与风险源。
(4)对负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职责的工作人员进行高水平培训的能力:国家对负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职责的医疗人员、志愿者、救援人员等要开展定期高水平培训,进行协同演练。
(5)对公众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育能力:国家建立健全各类教育和宣传制度,提升全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救与互救、预防与应急的素质。
(6)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保障能力:国家建立和健全经费准备、应急救援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储备、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和保险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通信保障能力:国家建立和健全统一高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信保障体系,形成完整、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传输渠道。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志愿服务与捐赠能力:提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愿意为人民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提供物资、资金、技术支持和捐赠的能力。
(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人才培养与研究开发能力:具备相应条件的教学科研机构培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专门人才的能力,教学科研机构和有关企业研究开发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具的能力。
5.2 监测与预警阶段的能力提升路径
监测与预警阶段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二阶段,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是及时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的前提。这一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系统运行能力:国家应当建立或者确定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系统,汇集、储存、分析、传输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在不同部门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交流与情报合作。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收集能力:国家通过多种途径收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有关部门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信息报告员,一旦获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责任主体清楚、报告渠道畅通、报告及时、报告内容完整、报告程序科学。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与风险快速评估能力:国家建立中立、权威、高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与风险评估机制,具有对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快速评估能力。
(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能力:国家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具有对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高效和准确监测能力。
(6)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能力:能够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精准确定相应的预警级别,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7)精准采取预警措施能力:能够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精准采用相应预警措施,有效消除产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因素,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级别精准调整能力:能够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和变化态势,及时精准调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级别,直至最终解除预警。
5.3 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的能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有效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害,防止事态扩大和次生、衍生事件的滋生。这一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
(1)有效处置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国家能够根据其特点和危害程度,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迅速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迅速将其消灭的能力。
(2)采取救助性应急措施的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国家采取救济、救助、帮助或者援助等应急措施能力。
(3)采取限制性应急措施的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国家采取限制公民和社会组织权利的应急措施能力。
(4)采取保护性应急措施的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国家采取保护国家机关、公共机构、公共设施和私人财产等的应急措施能力。
(5)采取保障性应急措施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国家采取的用以克服财力、物力和人力等不足的应急措施的能力。
5.4 事后恢复与重建阶段的能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的活动结束之后,并不意味着应对过程的结束,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后处理阶段,即事后恢复与重建阶段。在这一阶段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
(1)公民和社会组织合法权利的恢复能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应对过程中,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财产权、人身等权因受到行政机关或者其他主体的合法或者违法行为损害,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国家具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及时恢复公民和社会组织合法权利的能力。
(2)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物质设施恢复能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应对过程中,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物质生产生活设施可能受到损害,国家具有相应法律制度来及时帮助公民和社会组织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的能力。
(3)国家和集体公用公有设施恢复能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应对过程中,国家和集体的公用生产设施可能受到损害,国家具有相应法律制度来及时恢复公有和公用设施的能力。
(4)国家法律秩序恢复之能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或者发展过程中,因特定公民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破坏国家法律秩序,突发事件结束之后,国家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依法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的能力。
5.5 应急管理机构及其治理体系重新定位与设计
这部分主要包括建构集中统一的国家疾病控制中心,通过法律赋予其类似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那样的法律地位,享有直接对社会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权力;增强国家应急管理部的职责,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职责由国家卫健委调整到国家应急管理部;重新设计地方应急管理体系,增强地方应急管理厅的法律地位;重新设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体系,重新规划预警体制、机制和法制。
5.6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核心能力提升之途径
(1)提升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能力之途径
这一阶段主要通过设计或者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提升能力,主要的法律制度有:
①制定和修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制度;
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源调查、登记、评估、监控制度;
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培训和演练制度;
④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宣传教育制度;
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保障制度;
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人才培养制度;
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研发与奖励制度。
(2)提升监测与预警阶段能力之制度
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交流与情报合作制度;
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收集制度;
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制度;
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与风险快速评估制度;
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制度;
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
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措施制度。
(3)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能力提升之途径
①应急处置动员制度;
②救助性应急措施制度;
③限制性应急措施制度;
④保护性应急措施制度;
⑤保障性应急措施制度。
(4)事后恢复与重建阶段能力提升之途径
①公民和社会组织合法权利的恢复之制度;
②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物质设施恢复之制度;
③国家和集体公用公有设施恢复之制度;
④国家法律秩序恢复之制度。
致谢
感谢司法鉴定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的资助和支持。同时,文章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徐涤宇教授、魏永长副教授、曾益副教授、徐娟副教授、邹梦琪博士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Svoboda T,Henry B,Shulman L,et al.Public Health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during the Outbreak in Toronto[J].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4,350(23):2352-2361.
[2] Lumpkin J R,Miller Y K,Inglesby T,et al.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Health Security Preparedness Index[J].Bio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Biodefense Strategy,Practice,and Science,2013,11(1):81-87.
[3] Nelson C,Lurie N,Wasserman J,et al.Conceptualizing and defin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repar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7,97 (Supp1):S9-11.
[4] Li C,Sun M,Wang Y,et al.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ystem in China:Trends From 2002–2012[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6,106(12):2093-2102.
[5] Sun M,Xu N,Li C,et al.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Trends from 2002 to 2012[J].BMC Public Health,2018,18(1):474.
[6] Hu G Q,Rao K Q,Sun Z Q.A Preliminary Framework to Measur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J].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6,14(1):43-47.
[7] 王晓东,吴群红,郝艳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3,32(6):47-50.
[8] Mccabe O L,Barnett D J,Taylor H G,et al.Ready,Willing,and Able:A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reparedness System[J].Disaster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2010,4(2):161-168.
[9] Dausey D J,Buehler J W,Nicole L.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Tabletop Exercises to Assess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for Manmade and Naturally Occurring Biological Threats[J].Bmc Public Health,2007,7(1):1-9.
[10] Asch S M,Stoto M,Mendes,et al.A Review of Instruments Assessing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J].Public Health Reports,2005,120(5):532-542.
[11] Rosenfeld J.Is the Australian Hospital System Adequately Prepared for Terrorism?[J].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2005,183(11-12):567.
[12] Farazmand A.Handbook of Cris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M].New York:Marcel Dekker,Inc.,2001.
[13] Paton D,Jackson D.Developing Disaster Management Capability:An Assessment Centre Approach[J].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2002,11(2):115-122.
[14] William L,Waugh J,Gregory S.Collaboration and Leadership for effec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12(66):131-140.
[15] An Emergency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Canada[R].Public Safety Canada,2009.
[16] Comfort L K,Waugh W L,Cigler B A.Emergency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Emergence,Evolution,Expansion,and Future Direction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2,72(4):539-547.
[17] 韩传峰,叶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综合评价[J].自然灾害学报,2007(4):149-153.
[18] 杨青,田依林,宋英华.基于过程管理的城市灾害应急管理综合能力评价体系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7,261(3):103-106.
[19] 田军,邹沁,汪应洛.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4,17(11):97-108.
[20] Harris J K,Clements B.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Understand Missouri’s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lanners[J].Public Health Reports,2007,122(4):488-498.
[21] Duan W,Cao,et al.An ACP Approach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Using a Campus Outbreak of H1N1 Influenza as a Case Study[J].Systems,Man and Cybernetics: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2013,43(5):1028-1041.
[22] 王薇,曹亚.基于BP神经网络的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19):75-81.
[23] 胡象明,张智新.应急管理研究:理论探讨与政策创新的统一——“应急管理与政策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J].理论探讨,2007(1):111-112.
[24] 钟开斌,张佳.论应急预案的编制与管理[J].甘肃社会科学,2006(3):240-243.
[25] 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的演化历程与当前趋势[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7(6):11-20.
[26] 薛澜,刘冰.应急管理体系新挑战及其顶层设计[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10-14+129.
[27] 谈在祥,吴松婷,韩晓平.美国、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的借鉴及启示——兼论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J].卫生经济研究,2020(3):11-16.
https://doi.org/10.14055/j.cnki.33-1056/f.2020.03.017
[28] Waugh W L,Streib G.Collaboration and Leadership for Effec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66(s1):131-140.
[29] 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5(3):58-84+206.
[30] Henstra D.Evaluating Local Govern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grams:What Framework Should Public Managers Adopt? [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0:1540-6210.
[31] Kapucu N.Collabor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Better Community Organising,Better Publ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J].Disasters,2008,32(2):239-262.
[32] Drabek T E.Strategies for Coordinating Disaster Responses[D].Natur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Center,2003.
[33] Fitzpatrick P.Natural Disasters:Hurricanes[M].Santa Barbara,CA:ABC-CLIO,1991.
[34] Burby R J.Natural Hazards and Land Use:An Introduction[M]// R J Burby(Eds.).Cooperating with Nature:Confronting Natural Hazards with Land-Use and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Washington,DC:Joseph Henry Press,1998.
[35] Williams D E,Olaniran B A.Expanding the crisis planning function:Introducing elements of risk communication to crisis communication practice[J].Public Relations Review,1998,24(3):387-400.
[36] 高小平.整体性治理与应急管理:新的冲突与解决方案[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7(6):3-10.
[37] 李菲菲,庞素琳.基于治理理论视角的我国社区应急管理建设模式分析[J].管理评论,2015,27(2):197-208.
[38] Khan Y,Fazli G,Henry B,et al.The evidence base of primary research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reparedness:A scoping review and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Health policies,systems and management[J].BMC Public Health,2015,15(1):432.
[39] Salinsky E.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reparedness:Fundamentals of the system[EB/OL].National Health Policy Forum,2002-04-03.
[40] 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7):6-11.
[41] Venkatesh S,Memish Ziad A.Bioterrorism-a New Challenge for Public Healt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2003:212.
[42] 薛澜,钟开斌.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J].中国行政管理,2005(2):102-107.
[43] 刘雅文,叶琳,王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危机管理理论的应用[C]// 2004年SARS与禽流感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
[44] 贾学琼,高恩新.应急管理多元参与的动力与协调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11(1):70-73.
[45] Liang H,Xue Y.Investigat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Information System Initiatives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2004,73(9/10):675-685.
[46] 薛澜,朱琴.危机管理的国际借鉴:以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3(8):51-56.
[47] 董建新,余钧.公共危机预防投入的分析与对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中国应急管理,2010(12):20-24.
[48] 冯俏彬.我国应急财政资金管理的现状与改进对策[J].财政研究,2009(6):12-17.
[49] 王乐夫,马骏,郭正林.公共部门危机管理体制:以非典型肺炎事件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2003(7).
[50] 代颖,马祖军,郑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系统中的模糊多目标定位——路径问题研究[J].管理评论,2010,22(1):121-128.
[51]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2] 高小平,刘一弘.我国应急管理研究述评(上)[J].中国行政管理,2009(8):29-33.
[53] 高小平,刘一弘.我国应急管理研究述评(下)[J].中国行政管理,2009(9):19-22.
[54] 黄晓燕,陈颖,何智纯.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核心能力快速评估方法的研究和应用[J].中国卫生资源,2019,22(3):236-241.
[55] 雷晓康,安静,张茜茜.跨区域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内部应急协作的情景构建分析与优化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19(4):145-150.
[56] 刘辉,周慧文.社会突发性事件中面向农民的应急型社会保障研究——从“非典”事件中社会保障对农村人群的支持作用谈起[J].农业经济问题,2004(7):55-58+80.
[57] 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王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35.
[58] 吕孝礼,张海波,钟开斌.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危机管理研究——现状、趋势和未来方向[J].公共管理学报,2012,9(3):112-121+128.
[59] 诺曼·奥古斯丁.危机管理[M].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
[60] 滕五晓,夏剑霺.基于危机管理模式的政府应急管理体制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2):22-26.
[61] 王陇德.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况、趋势分析及应对策略[J].中国应急管理,2007(2):21-24.
[62] 肖鹏军.公共危机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
[63] 游志斌.美国第三代全国突发事件管理系统的变革重点:统一行动[J].中国行政管理,2019(2):135-139.
[64] 钟开斌.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J].中国行政管理,2005(2):102-107.
[65] 钟开斌.中国应急管理机构的演进与发展:基于协调视角的观察[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8,7(6):21-36.
[66] Col J M.Managing Disasters: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7,67(s1):114-124.
[67] Donahue A K,Joyce P G.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with an Application to Federal Budgeting[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1,61(6):728-740.
[68] Drabek T E,Hoetmer G J.Emergency Management: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for Local Government[M].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91.
[69] Gunes A E,Kovel J P.Using GI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Operations[J].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2000,126(3):136-149.
[70] Hu J,Zeng A Z,Zhao L.A Comparative Study of Public-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J].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2009,109(7):976-992.
[71] Ian I.Mitroff,Managing Crisis Before Happened[M].New York: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2001:34.
[72] National Health Security Preparedness Index Team.National Health Security Preparedness Index[EB/OL].(2018-03-01).[2019-01-22].
https://nhspi.org/wp-ontent/uploads/2018/03/2017-Measure-List-01Mar2018.pdf.
[73] Peters D H,Hanssen O,Gutierrez J,et al.Financing Common Goods for Health:Core Government Functions in Health Emergency a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J].Health Systems & Reform,2019,5(4):307-321.
[74] Reddick C.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Preparedness and Planning in US States[J].Disasters,2011,35(1):45-61.
[75] Revere D.Nelson K,Thiede H,et al.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Communications with Health Care Providers:A Literature Review[J].BMC Public Health,2011,11(1):337.
[76] Rose D A,Murthy S,Brooks J,et al.The Evolu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as a Field of Practice[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7,107(S2):S126-S133.
[77] Seeger M W,Pechta L E,Price S M,et al.A Conceptual Model for Evaluating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 in Public Health[J].Health Security,2018,16(3):193-203.
[7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Toolkit for Assessing Health-System Capacity for Crisis Management [EB/OL].(2014-04-04).[2019-01-22].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8/157886/e96187.pdf.
[79] Yasmin,Khan,Tracey,et al.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reparedness:A Framework to Promote Resilience[J].Bmc Public Health,2018.